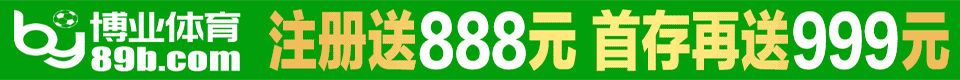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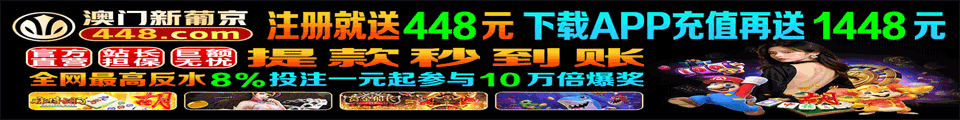


推荐观阅
友情推荐
我的激情
和天天进入冷战有一个星期了,彼此谁都不开口说话,我被这沉默压迫的要窒息了。
我坐在梳妆台前整理我的头髮,心里在盘思着怎么打破这僵局。
「天天,我的头髮被衣服的拉练缠住了。」我用极不自然的夹杂着一丝的颤音说着。
身后一阵沉默,沉默的可怕,忽然我看见地上有一个影子在向我悄无声息的逼近。
这不是我的幻觉,我感到有一双冰冷的手拈起我的头髮,其实并没有缠住,很容易的就分开了。
我默默的站起身,做了个手势让他坐下,很庆幸,他遵从了。
他凝视着我,摇曳不定,我挪开视线,掩饰着自己片刻的慌乱。
我深深的吸了口气,意识到自己现在应该做什么……
我穿着黑色的薄丝袜,两条笔直的有弹性的袜筒一直延伸到了有花边的袜带上,绕在我这纤细裸露的柔腰上。半圆型黑色花边的小小菱形,恰到好处的遮住我那饱满的耻骨隆起,动人心玄的收入修长比例均匀的大腿间,并盖住了我的阴唇。
我两腿叉开站在他面前只有一米的地方,褪去了我的吊带裙,手移向乳罩,轻轻托起我的乳房。
他只是静静的坐着,瞧着。我的脉搏疾跳着,他可能会拒绝我,同时厌烦的走开。这次我的引诱挑逗更加直接,他会不会……
两腿之间紧紧的花边吊带,使我阴蒂稍动一下就会敏感的颤慄,我把手伸到背后解开胸罩的挂钩,当它落下时,我抓住它,防护似的按在胸前。
我感觉到乳头浑圆硬挺着,它们渴望他用口把他们吸吮的更加翘立。我期盼着他的唇来亲吻,可是他仍没有动静。
我还得继续遮掩一段时间,我祈祷着他不要离去,如果他还要走的话,我就投进他的怀中,用身体挡着他,可是他现在却是平静的,没有露出生气的神色,看来还没有必要加快速度。
我靠近他一些,转过身,让乳罩脱落下来,用食指勾住,回过头,悬晃在他的面前,然后让它飘落在他拱起的膝盖上。我把预先缠在手腕上的髮带拿下来,抬起手臂,把头髮束起来。
一个暖暖的身体紧紧的贴在我的背后,我不由吸了口气。他的手从我手臂上滑了进去,拥着了我的乳房。食指和拇指捉住乳头,轻轻的搓揉起来。
我又深深的吸了口气,把头向后仰去。他一句话未说,此时此刻,任何的话语都显的是多余的,这一瞬间,所有的话语都溶入了以往爱恋的回味中……
他把嘴贴在我的肩上,亲吻着我滚烫的皮肤,我微微的颤抖着。
我转过身,将乳房毫无遮掩的展入在他的注视下,带着一丝的迷惘,他又退后,仔细的瞧着它们,随后他跪在我面前,轮流的吮吸亲吻着乳头。舌尖飞快的在乳圈四周舔着直到每根粗短的肌肉纤维有力的鼓胀起来。
我轻轻的托着他的脸庞,深深包含着爱恋的凝视着他,我把他牵到凳子上坐下,我的大腿朝两边分开,几乎都触及他的膝盖,我的黑色隆起向前冲了出去。
我眼里透射出兴奋的光芒,俯眼向下看着用牙齿轻咬着下嘴唇。我的手指伸成扇形下滑落到了小腹上,接着滑到大腿外侧然后慢慢的,充满煽情,移向两侧的吊带,解开了带子,让它们静静的落在地板上我的指尖又落到充满弹性的内裤上,把它拉倒臀部以下,直到黑色的花边的内裤被一片黑色的阴毛替代。
我感觉到了体内汹涌澎湃的兴奋热浪。他的雄性蛊惑使我急切地渴望得到他正在迅速膨起的阳具。我帮他慢慢的脱掉上衣,起身站在他的面前,他也随之起身,我半跪在他的面前,把他的裤链拉开,解松裤子,把他硬绷绷的阳具释放了出来。
我不禁颤慄得更加厉害,我想把牙齿深深陷进他的肌肉里,用嘴去感受那份坚硬,我强忍着冲动。
他现在完全赤裸了,正在引诱着我,虽然他的胜是那么麻木不仁,但当他看到我的手指滑进我大腿间黑色的缝隙中时,他的眼里微微闪出一丝需求的眼神。
我的手指是那么自然的找到了阴核,我的阴唇象嘴似的不停的吮吸着这根手指,我的手指开始抽动着,伸进去再慢慢的拉出来,这种感觉几乎要超过从他那里得到的感受。
我知道他会变的更加兴奋,这种淫霏的行为使我娇喘吁吁,太阳穴的血管也紧绷着,我感到了口舌乾燥。
他又坐在那里,光滑深红色的龟头怒张着,它像似硬硬的布满血管的长矛蛇样的对我竖立着,我忍不住浑身剧烈哆嗦起来。
我极想把它含入口中,整个吞进去我想感受着喷涌的热量和在咽喉中细细流淌的感觉,但我拚命克制着这种想法。
我下面性感中心爱液溢流,阴核也更加敏感。我背过身去,把内裤从腿上脱去用手指勾着它抛掉,它飘落在地上,我张开双腿,弯腰又捡了起来,这样似乎带着无限的兴奋,向坐在只有手臂远的他表现出了直接了当,最亲密的应诺。接着我再次的把手指压进大腿间。
当我把大腿更阔的伸展时,长袜紧紧裹着我,大腿内侧战慄着,腰下的洞穴在这种浪蕩的姿势下更加绷紧,他的阴茎似乎更粗壮,更伸长而且慾望更强烈,我知道他会它把插到我等待的阴道里,我将去感受它的热量和力量。
我弯下腰,两腿张开,在黑色长袜的映衬下,细腻的茸毛象柔软的覆盖上黑色丝缎的光泽,两片圆润饱满的阴唇,我慢慢的极具诱惑力的褪去长袜,这些景象强烈的刺激着他,他为之震颤,太阳穴也紧紧鼓凸着。
他几乎是向我冲过来一样。在我的身后跪下来。把嘴唇贴到我给予他的柔软的阴唇上,吸吮着。他的舌头伸出来顾及到我充满性慾的阴核上,它肿胀着伸展着来被他欣赏。
我呻吟起来,过了许多分钟他还逗留在那里,舔吻着那暖暖的性感器官,用舌间刺激着它。随着每一次滑动,我都抖动着,阴唇痉挛的一张一合。
他抬起身用手搂着我的臀部摇晃着我,再把臀部翻转到最顶上,用拇指撬阴唇。那上面闪烁着他的唾液和我兴奋渗涌出的爱液。他把手指深深的伸进去,沾上湿湿的液体,涂抹在他自己的长矛上,他驾权着长矛狠狠的刺入我的身体里,尽它的所能。
我感受到了那个热乎乎的阳具已深深的插入了体内。我手撑着坐椅后,尽量加宽自己站力姿势,阴道紧紧夹着坚硬的阳具,身体用力的向后挺冲着,极力不放过那长长的每一寸。
他没有抽动,没有不停的伸进抽出。他只是停留在那里面,手指爱抚着我那向上冲顶的臀部,拇指使劲在隐秘的裂缝里压着。而这一切似乎他仅仅想去体验拥有我的感觉,也给予我那种想像中塞满的愉快感。
我不能让他停在那里,这对我来说还远远不够,我需要真正感受到他在体内搅动的感受,要真正感受到他的紧绷和喷射的感觉。我的骨盆也开始摇动,并用力的夹着,吮吸着他的阳具,身体不停的来回扭动。
他用手环抱着我的肩膀,把我的身体拉直起来,背部贴着他的胸膛,他的手臂从下面滑上去,捧着我的双乳,他的男根在我的体内紧紧绷着硬硬的毛根向上揉搓着我的花蕾,让它感到美妙无比的快感。
我知道我已经被他彻底的俘虏了,「给我……天天……我要……」我嘶哑的叫着,喘息着,这是他帮我挪开头髮后,我首先发出来的话,我扭过头,紧紧贴在他的脸上。
他贴在我的耳边低声说道:「好吧,我来给你……」他带着快感拨弄着我的乳头。
他忽然轻轻的从我的体内退出,没等我提出抗议,把我转过来,用手托着我我的背和腿,把我整个横抱起来,边亲吻着我的额头,边把我抱到床上。
他向前趴到我的身上,我抬头看着他,他的阴茎深红色的龟头沾着我的爱液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慢慢的把嘴凑向我,整个身体压在我的身上,接着再一次的深深滑入我的身体里面,他用手肘支撑着,盯着我的眼睛。
我轻声的问道:「你是不是已经宽恕我犯的错误了。」
他用难以琢磨的语气说:「那你要乖啊,要听话,我才会爽你的啊,听见了吗?」
我温柔大胆的亲吻他作为回答,阴道肌肉强调似的夹了一夹他侵入的阳具几下。
「当然我知道了,我会听话的,天天,我发觉我已经离不开你了,我是那么的需要你,也请你原谅我所犯的错误,原谅我的叛逆。」我轻轻吻了他的鼻尖,「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虽然我有时对你还想当只未驯服的小动物。」
他轻轻的说着:「我爱你,真要命,爱你这个烫手的山芋……」
我凝视着这个正把阳具插入我体内的男人,「我也爱你……你对我充满着魔力……」
我动情的说着,眼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但我不能再玩下去了,马上来要我,要狠狠的,长久的。」
我的嘴紧紧的拥吻着他,开始使劲地扭动臀部,并把阴核抵在他拨起物的根部。他双手搂起我的臀部,使我挺起来。我往回弯曲着腿,加宽姿势让他彻底的进入,他现在可以毫无阻挡的全部进入我的体内。我把自己全部献给了他,包括我的灵魂深处……
当我感到他的手指在我的小小裂缝上施加压力时,一股愉快的震颤迅速传遍身上每个角落。起先,轻轻的,他摆弄他的长矛和手指,一进一出。我完全的伸展开来,疯狂的把腿弯曲回来,膝盖碰到了胸部。
现在,他加快了速度,每一击都更深更狠。我颤动着,拚命蠕动着我那性感中心的阴道,有节奏的收紧放鬆。我的指甲紧抓着他的后背,一边拉扯着他,让他更深的进入体内。
他加快了他的冲刺。
他抽动着,一遍一遍的冲刺着。
我把头伸起紧紧咬住他的肩膀。
他发出咆哮,冲刺着,更深,更狠,更长。
「操我……天天……操我……快……!!!」
我苦苦的哀嚷着。
我刺激着他……
现在一切已经失去控制了,他奋力的向前冲刺,把长矛彻底的插进去,再完全的抽出来。他的耻骨也在我上面摩擦着,用力不停的撞击着我,随着每一次强有力的侵入,彼此发出一串串快感的呻吟声。
我抖动着,每一次抽动越来越变的疯狂和更兇猛的攻击。我们都忘乎所以的发出淫霏声。
他已气喘吁吁,当那股强力在我的身体里最大限度的来回抽动时,他的手指也深深的插进我紧紧的洞穴里。
「啊……」我哭叫起来,但是不停的发出一股强烈的快感,传遍我的全身。
「再猛些……天天………猛烈的操我……请不要停下……我不让你停下……快……」
我不停的吸泣着,从肺里发出的喘息声,伴随着每一次抽动声,一同从嗓眼里挤出。
现在,随着每次的冲击,他都发出「操」的咆哮声,疯狂,猛烈的动荡着进入我,不停死死的抓着我朝向他。当那能量堆积在性爱的焦点上,我开始进入濒临边缘的紧张状态。
我每次挺动,都紧紧拉着他,挨近他,极力想冲破那道由紧张造成的堤围。
他叫喊出来:「操……操……」
我喘着气「对」在每一个回合上。
他的下腹起伏着,不停升上去,降下来。我奋力的蠕动着臀部,迎合着他的冲击。他落下去,我也跟着落下去。
这种节奏变的越来越激昂,而且狂乱起来,他像是个活塞,在他自身的动力下,难以停顿下来。
我向上挺着,扭动着,……
「操……」
「啊……」
终于在这种疯狂的动作和叫喊声冲击下,堤围终于被突破了。
我们两同时一起达到了性爱的顶点,爱浓肉体狂烈敲击的手足以及尖锐地喘气。他射精冲击力以及在他体内的热量,使我不自禁的颤动着,性爱的快感上升到顶点终于爆发了,迅速电击似的通向全身。我们的小腹贴在一起,同时痉挛的起伏着。
随着每次收缩又引起小小的抽动,直到慢慢的鬆弛下来,进入一种极大喜悦的漂浮状态中去了。他也彻底的崩溃了,但他仍紧紧的贴在我的身上,还再自发的抽搐着,脉动的阴茎也缓缓的软耸下来。我们的嘴紧紧的簇拥在一起。
我用舌头模仿他充满慾望时的阳具所做的,在他口里吸吮,伸动着。我深深的凝望着,身体放鬆下来,在我的深处还在品嚐着滴答抖动的滋味。
一切都做完了。我已经被爱过,被操过;同样也爱过,操过。
我们静静的躺着,我的手臂环抱着他的脖子,他用手支起身体,不停俯下身亲吻着我。
他感到了满足,当然能彻底的征服我也有一定的影响,他也深深的知道,我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和灵魂深处的都给了他。
他体贴的把我转了过去,背对着他,手枕着他的手臂,用我最爱的方式抱着我,手指和我的手指互相交叉,我的头髮被汗水粘湿了,他温柔的撩起粘在颈部的头髮,轻轻的吸着我身上的味道,「芸儿,刚才舒服吗?」
「嗯……」
「芸儿?」
「天天,我想我的身体已经给了你满意的答覆了。」我喃喃道。
「天天,爱我吗?」
「爱的,我爱芸儿。」
我满足的笑了。
「芸儿,你累了?」
「嗯……」
「好,乖,我就这么抱着你睡。」他爱怜的说着。
……
我的胃一阵咕噜叫着,射进来的光线说明现在已经是早晨了。我轻轻的把天天的腿推开,起身走进盥洗室,我拉开了灯,想沖个澡。水有点烫,热水沖到我的胸部,让我感到惬意无比,我感到恢复了体力,也非常的满足。水向下流过小腹,从耻毛汇成一条细流。
我用香皂擦着肌肤,润滑的皮肤在擦拭下传来些许的快感,全身禁不住微微抖动。当我用香波梳洗头髮时,两只宽大的手掌从我的臂下伸入,拥住了我的双乳,乳头也被夹入手指中,一张性感的嘴贴在我的颈脖上。我在任何地方都会认识这双手的。
「早啊,芸儿,为什么不多睡一会?」他凝视着我的双肩,呼吸沉重起来,他的手穿过香皂沫,滑到我的V行型区。
我扭过头,封住了他的双唇。
「要爱我,因为我爱你啊~~~」我喃喃道。
「嗯,我会的。」他边回答着边将淋蓬头从钩上取下,把热水直接喷到我的胸脯上。
我颤慄着,他接着往下喷洒到小腹和凸起的阴部。细细的喷泉渐渐使我的阴蒂酥痒起来。我开始抖动,我张开双腿,露出阴唇让这种愉快也喷洒上去。
他仍在我的身后,将喷头对準他昨晚伸入过的欢乐洞穴让水线在压力下冲进去,我叉开双腿,好让水线射的更深入。哦,他继续把喷头挨近这已经带着快感肿胀充血的阴唇。
当热水不断喷射到每片肿胀的阴唇上时,我开始剧烈抽搐,可是他又故意的挂起了淋蓬头。我呻吟着站直身,转朝着他。
「你为什么那样做?我都快要被炸成碎片了。」
他拍拍颈脖,「为什么喷淋头会令你这么开心?我要你因为我的阴茎在里面而粉身碎骨,还有手指插进你臀部里。」
他嬉戏的轻吮着我的乳头。
「变态啊,你!」我伸出手摀住他的睪丸手中热乎乎的液体已令他兴奋。我又把头放入喷头下,闭起眼睛,喘着气。
「天天,你醒的真快。」
「呵呵,我是闻到一种气味,我想肯定是你分泌的。」
「我?我分泌什么啊?」
「你身体的气味和你的性气啊,令我癡迷啊。」
「呵呵,你也一样啊,令我疯狂啊。」他垂下眼睛看着我。
我脸上充满喜悦,双眼闪烁光芒。他爱恋的吻着我的唇,喷淋水顺着我们的嘴角流淌下来。
我拿起香皂给他擦着,双手含着温馨的诱惑,滑过胸部和双腿,最后在开始往他的阴囊上涂抹着香皂,又用手握住阴茎涂抹着,一边用手指端拨弄着龟头和阴囊皮上凹凸不平的肉粒。
我边用清水为他沖洗,一边把包皮拉上来遮住龟头。
然后我亲吻着龟头,包皮滑下来,阴茎变的又粗又硬。我的手指滑进了他的双腿之间,手指伸进了臀部的裂缝里,我的食指在他的阴囊根部挤压。他呻吟起来,将身子往前挺着,我不停的用手抚弄着。
「天天,我想我对你做的事是最刺激的吧?」
「别那么自信,我不会轻易上钩的啊。」
我咯咯的笑了,接着跪下来舔吮着他骄傲的形似蘑菇的龟头。
「我要说什么才能诱惑你呢?难道要我直接说天天,操我?」
我又忍不住咯咯的笑起来,狠狠的在阳具上吮吸一口。
「我要让他又粗又硬,我不让你停下来,直到你向我求饶。」
「呵呵,好啊,我到要看一下,究竟是谁先求饶啊?」
我贴上了他的身体,双臂搂住他的肩膀。喷淋水喷在我的头上,我再一次吻着,闭上了眼睛。
他关上了水阀,一只胳膊拥着我的肩,另一只手搂着双腿,将我抱着离开了喷淋头,让我靠在了台盆边上我的一只手朝后撑着,用脚后跟抵住了台盆下的边缘。
「不,芸儿,转过去,面对着镜子。我喜欢看着你享受的样子。」
「哦……不~~~~」我羞涩的说道。
「小傻瓜,这有什么好害羞的啊?你是我的啊。」
他把我转过身,用一只手臂环绕着我的腰而将我轻轻往后仰,并且把他的中指沿着我充血的私处内侧滑动,并使他的食指和无名指坚实的顺着我的阴唇外侧而轻触压揉。
我喘息着,而当他把嘴压在我的唇上吻我的时候,他环着我的腰的手更紧更实。兴奋的感觉在我的体内流动释放,并且威胁的要吞噬了我。依然是他控制着轻慢,他的手指进去的更深了。
我感觉到我的体内的湿滑新腻,更有体内的肌肉咬紧密贴着他的手指,向上吮吸着他,他用他的舌头推开了我的牙齿,继续在我的双腿持续游动之际,搜寻着我的舌头。
我张开嘴期待着他的舌头,并且用手臂环绕着他的脖子。而他的手从我的腰际滑下掠取了我的双臂,并且用力抓牢它们。我可以感受到他的阴茎的强硬了。
我略微的伸展身体,让他在我体内的手指能挺到我阴道的顶端。他的手指在我狭道深处的挪动震撼了我。
我的嘴唇分的更开了,以求能接受他的舌头更多,而我颤抖的双腿则用力的裂开着。他用另一个手指滑进她,他的拇指开始在我的阴核上轻柔的滑溜和捏,而另一个手指,则在我的阴唇和后门的区域来回探索着。他把我拉的更近了,好让他的手指可以逐渐按摩我湿润泛潮的洞穴。
「芸儿,自己看镜子里的你,真的好骚啊,骚的让我不忍放手啊。」
「哦,不,不要放手……」我激动的呓语着。
他慢慢的,带着无限的小心,他的手指由我背后的洞孔进入了。
「啊……」我忍不住叫出声来。
「啊~~不~~不要……」
我觉的我整个身体象被刺穿了我的身体本能的向前冲去,他把我抱的更紧,「芸儿,不要动,我很轻的,不会弄疼你的,我也捨不得啊。」
我迷迷糊糊的听着他在我耳边细诉,顺从着他的话:「乖~~~芸儿……放松……对……放鬆……」
他轻声的引导着我,「嗯……乖~~~现在好点了吧?」
「嗯……」我点了点头。
他亲吻着我,用舌尖滑过我脸上的每个部位用牙齿轻咬着我的耳坠,来消除我内心的些许的恐惧。
「哦……」我发出了呻吟,他知道我在逐步的适应了,他慢慢的抽动着。
「啊……」我完完全全的失去控制,我整个人都在振动着。
我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他的唇在我嘴上的触感,他的吹弹和对我的舌头的戳刺。
「哦~~不……不要……」我求饶道:「天天,不要啊……我好痛啊……」
我的泪水落了下来。
「哦,芸儿。乖~~不哭,我出来,慢慢的出来。」他爱怜的说着:「不哭了,芸儿,等你以后完全做好準备了,再让我完全的进入。嗯?」
「嗯,好的,天天,我爱你,我愿意把我的身体每个部位都奉献给你。」
「嗯,好的。」他爱怜的用舌头舔乾我的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