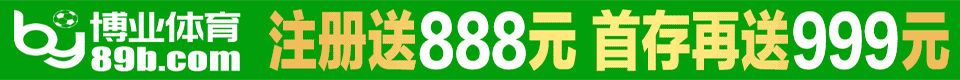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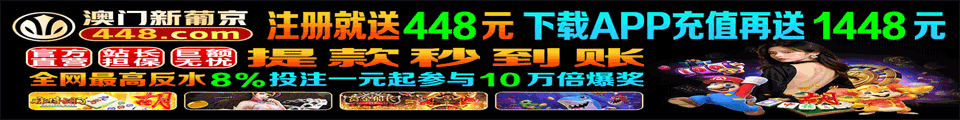


推荐观阅
友情推荐
跟阿姨洗澡
阿姨,四十多岁了,可是一点都看不出来,翘臀丰乳、俏面泛春,倒像是一位花信少妇。虽然阿姨诱人的身体总是包在衣物中,可是无论阿姨穿着什么服装,一米59,三围33。25。35只要是一看见阿姨,我一闭上眼,脑中就是她赤裸裸褪出衣物的身体无时无刻都能让我的肉棒充血、亢奋……姨丈去世多年又无儿女,我多时?机会到阿姨字家作客,可以多窥窥呀姨诱人的胴体……记得有一天因天太热,阿姨穿了一真丝的白色薄长裙,里面的黑色胸罩依稀可见。坐在我旁边吃饭,在她低头的时候,我从她那宽松的领口瞧见了那几乎奔跳而出的两颗雪白、浑圆的乳房,高耸雪白的双乳挤成了一道紧密的乳沟,阵阵扑鼻的乳香与脂粉味令我全身血液加速流窜,这一幕确实让我梦遗了几回。
今天,大好的机会来了!
「呀!好痛呀!」
阿姨粉脸变白,很痛苦的喊叫!
阿姨今天和平日一样,穿着一件舒服T-shirt和一条短裙,起床後便在家中打扫乾净,一不小心摔倒在地上,十分痛楚。我刚巧在她家,我看到阿姨倒在地上,我迅速地扶起阿姨,和阿姨一起到医院。医生说阿姨两只手腕受伤,要用药包住,不能碰水也不能动。
我淫光满面说:
「由于你双手不能动,阿姨这几天不如让我照顾你?」阿姨犹豫了一下。
「让我来吧,阿姨。」我真诚的说。
於是阿姨便答应了。
回家后,阿姨准备上厕所,当走进厕所后,问题了来。阿姨双手不能动,怎样上厕所?
阿姨大声喊道:「虾仔走过来好吗?」
当我过来後,阿姨尴尬的小声说:
「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帮我?」我心里知道上厕所问题的,但假装不知道。
「什么事啊?」
阿姨红着脸低下头用沙哑的声音说。
「厕所」
「什么事啊?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这…我实在是说不出口啊!」阿姨回答。
「哦……原来如此……那我能帮上什么忙呢?」「你可否进来,帮我……」阿姨红着脸说。
然后我慢慢地走进厕所,蹲下来,双手拉下阿姨的短裙,接着我缓缓的脱下白色内裤 ,短裙和白色三角裤一起拉到膝下。
我看得全身血液加速流窜,裤中硬挺的大鸡巴硬如铁般。
这时阿姨的腰部以下全都裸露了,下体正面的对着我,害羞得呀姨把眼睛闭起来。
阿姨因为脚打开,使得她的小穴也跟着开开的!两片粉嫩的阴唇还是纷红色的,阿姨的阴户这时一览无遗,阿姨的阴户保养的很好,外面的大阴唇还保持着白嫩的肉色,旁边长满幼细的黑毛,细白的大腿,丰满的臀部,光滑的肌肤,只见小馒头似的阴阜,阴毛丛生了一大片,乌黑亮丽,诱惑迷人极了,突然我伸手摸了一下阿姨的大腿,阿姨震了一下。
「谢谢……」阿姨害羞的说
呀姨急忙坐在马桶上,深深叹一口气。
『啪……啪……』
我屏息静听的听阿姨的排尿声。
「虾仔……拜托……能……给我……擦吗?」阿姨的声音显得很微弱。
我点点头,立刻拿卫生纸。
阿姨因为难为情因此把脸转开,我战战竞竞的把拿卫生纸的手接近阿姨的胯下,在阿姨的小穴上轻轻摩擦。
阿姨此时被我之举动,使得她又惊又羞,她颤抖着,抽慉着全身的血液开始沸腾。
虽然隔一层卫生纸,但从手指明确的能感受出柔软的肉感,我也显得狼狈。我拿着卫生纸擦拭着阴道周围,看着卫生纸渐渐地由乾转为湿,整张卫生纸充满了水分,我默默的用卫生纸抚摸阿姨的下阴。柔柔的阴毛、软软的阴阜,我用三根手指轻轻来回抚弄碰触阿姨的阴唇。别人手指沿着肉缝抚摸的感觉,使阿姨的身体忍不住颤抖。
「擦好了。」
把微微吸收水分的卫生纸丢马桶里。
「再…一次……」阿姨为了擦干净,咬紧牙关忍受羞耻。
确实擦过一次,可是太轻,最重要的部分还是湿的,我默默的又拿卫生纸。需要更深更用力的擦。我仍旧默默的把手插入阿姨的双腿间,拿卫生纸的手压在胯下。阿姨闭紧嘴唇拼命的忍耐鸣咽声。我手上用力,几乎要把卫生纸塞入阴户里。我再用手指轻拨分开阿姨的阴唇,浓密黑亮的阴毛已遮掩不住那肥美略粉红色的私密处,手指毫无疑问的碰到温湿的肉上,我不断加大动作,不停来回作着穿插抚弄的动作,就这样用力擦过去。
「唔……可以啦……谢谢…」阿姨低着头说。
我把卫生纸从阿姨双腿之间去入马桶里,压下水开关。阿姨却狼狈死了,马上站起来,但来不及把内裤拉上去,只好夹紧双腿坐着。
阿姨脸色绯红,双脚夹得紧紧的。
到了晚上,阿姨是一个十分喜爱清洁的人,已一天没洗澡了,阿姨羞涩的叫我帮她洗澡。
「虾仔,我又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帮我?」「什么事?」
「你可帮我洗澡吗?」阿姨犹豫了一下,终于忍不住了,涨红了脸小声说。
「太麻烦了,这样吧,不如你和我一起洗好不好?」我故意逗阿姨。
阿姨红着脸,羞涩的摇了摇头。
「害羞甚么?我和你一起洗吧!」
阿姨害羞的点点头。
然后我和阿姨走进厕所,我和阿姨已感到些许的刺激感,我缓缓的脱掉阿姨的上衣,丰满的胸部充满整个乳白色的内衣,白皙光滑的肌肤,此时更是显的迷人,阿姨看着连自己都很满意的胸部,我更进一步的脱掉了呀姨的内衣,两个圆滚滚的乳房已脱离束缚,乳头已微微的涨大,阿姨害羞的半遮半掩着。
此时我伸手脱下阿姨三角裤,阿姨胯下那丛浓密乌黑的阴毛纤毫毕现,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时阿姨全身赤裸的站在我的面前。
我仔细的瞧片阿姨身上每一寸肌肤,阿姨被我瞧的有些害臊,只好羞怯的站在那而一动也不动的像个木头人,不愿与我相对。
美艳的俏脸红通通的,水汪汪的大眼精,微翘的嘴唇,阿姨那丰腴雪白的乳房正好一览无遗,乳房肥大丰满,两颗吊锺型的肥乳白皙赛雪,连青筋都隐约可见,乳头紫红硕大尤如葡萄,粉腿浑圆白皙,再加上丰腴成熟的胴体,及身上散发出的一股美肉味,我看得神魂飘荡,欲火如焚。
「绝对一流!太美了!」我看着阿姨的双乳,赞叹道。
「……」 阿姨没有出声。
我迅速的脱下自己的衣服和三角裤,我下身那东西,已经直挺挺的勃起,黑乎乎的,又长又粗!阿姨也大吃一惊!
阿姨 “啊!”的惊叫一声,伸手掩嘴,脸上飞红。
我们二人走进浴缸内,我拿起花洒,将水浇在阿姨身上,然后我就挤出一些浴皂,就从阿姨背後慢慢地擦拭呀姨身上。
阿姨除了姨丈外,还是第一次被别的男这样的搂着、摸着,从我摸揉乳房的手法和男性身上的体温,使阿姨全身酥麻 而微微颤抖。
我再挤出一些液体浴皂,往阿姨的胸部擦去,把阿姨的乳房涂得满是泡泡,跟着便用手轻慢的搓揉着。我的手伸过阿姨的腋下,手掌压在阿姨的乳房上,我感觉摸在手上既柔软又有弹性。
慢慢地我开始搓捏洗弄着阿姨胸前那两颗令男人垂涎的丰满肉球,有时还会肆意的玩弄挑逗着阿姨那极为敏感的粉红乳头,被我如此搓捏着双乳的呀姨,不但不觉得有丝毫的不快与被侵犯的感觉,反而轻闭双眼像是在享受着我的挑逗,甚至不做任何抗拒。
「啊…啊…啊…」阿姨娇羞的闭上那双勾魂的美目。
我将手轻轻的贴在阿姨柔软圆润的豪乳上面,揉弄起来,乳房白嫩的肌肉向左右歪曲,由於乳头在我的手摩擦而觉得甜美疼痛。
此时我左手的手指已靠在右边乳头上,轻轻的捏一下,然么顺时钟转个几圈,如珍珠般的乳头被我的手玩弄的慢慢变形,阿姨感到甜美的兴奋感已扩散到体内,我愈加用力地用手指夹住乳珠揉按挤压着。乳头变得坚硬起来。而淡淡的红黑色也逐渐转成深红色,一阵强烈的刺激感冲到脑中,我弄着乳房的手指缓换的动作,突然转变成激烈的爱抚,阿姨娇躯燃烧着,从来不曾有过的淫靡快感,使得整个背部抖动起来。
「嗯……嗯……啊……呀……」
阿姨的呼吸越来越沈重,嘴里的淫荡呻吟声也越来越大声。
这时我的大鸡巴偏偏贴在阿姨的肥臀边,硬翘的顶着,看着阿姨一动不动被自己侵犯,粉脸飞红,我胆子也大了起来,想起刚才阿姨的一双媚眼看着自己大鸡巴时的神情,一定是多时已经没有男人来触摸,而春心荡漾需要男人的大鸡巴慰藉,于是左手指改捏大奶头,阿姨的大奶头被捏得硬挺起来,铁一样硬的大鸡巴一翘一翘的在阿姨的肥臀后一顶一顶,「啊…啊…啊…」
使得阿姨娇喘连连,而我并不以此而满足,同时右手也开始往下移动。
「阿姨,我要洗你下面了。」
一听到我这般说道,阿姨下半身的嫩屄及屁眼立即一阵肉紧及强烈的骚痒,并且从粉嫩敏感的肉屄内缓缓地流出淫汁。
我慢慢的移到了阿姨的小腹了,阿姨还是没反应﹐我也觉得很意外,但也没想这么多。
我将手指头在下腹的肚脐处扫了一下,这一来使的原本兴奋的肉体显的更加急躁。我便以颤抖的手,开始轻轻的擦一擦阿姨那浓厚的耻毛,缓缓的移到股间炽热的浪屄,「唔……」阿姨微微一震,鼻息迟缓沈重起来。
我的手指滑近双股间温热的细缝,接着慢慢轻抚中间的凹缝,上下来回轻慢的抚摸着……阿姨此时肉缝中早已淫水泛滥,脑中更是有阵阵的电流穿过全身,我的手指移到肉缝的顶端,摸到一颗如红豆般大小的微突粒,我当然知道这就是女人最刺激的地方,开始轻轻的转圆圈,又是一阵更强烈的电流穿透全身……阿姨缓缓的闭上眼睛,全身轻轻地开始颤抖。
此时我从阿姨背后一把,俩人的灼热肉体紧紧地贴在一起,当然我的肉棒早又紧贴在阿姨的屁股沟上,我那抹着沐浴乳泡沫的双手已经轻轻搓洗着阿姨私处上方极为茂盛的阴毛,我将相当杂乱的耻部阴毛清洗过后,目标就转向阿姨的嫩屄,我将阿姨的嫩屄给分了开来,首先就用着手指搓抚着阿姨全身最为敏感的性感带。阴核,阿姨那早已成熟的肉体那里能够忍受的住我在她阴蒂的挑逗攻击,她的炽热性欲再度迅速充斥全身,此时经我抚摸玩弄阴核,肉屄内立即不停流出大量的淫水。
阿姨的身体又抖了一下,抬起头望了我一眼,但见阿姨脸颊泛红,眼神迷蒙,阿姨看了我一下,又害羞的把头低下靠在肩上,我感觉得出阿姨全身发烫,呼吸逐渐急促,胸膛那二颗乳球正随着呼吸而上下起伏。阿姨又看看我的鸡巴,又粗又长,又爱又怕,粉颊泛红,全身颤抖,低首垂目、不言不语。
这时的我根本早就不像是在帮阿姨洗澡,而是赤裸裸地在挑逗玩弄着阿姨那成熟的肉体,而阿姨也已被我那双极有爱抚技巧的手渐渐挑逗到高潮境界。
「…阿姨…你舒服吗?…」
「……」阿姨没有出声。
「…阿姨……姨丈去世已经很多年了,况且一个四十多岁的成熟女人正是性欲强盛的时候,让我为你舒服舒服吧!」阿姨低着头又没有出声。
「你已经出了很多水了!那里都湿漉漉的呢!…」我兴奋的说。
阿姨思索着,她需要一根强而有力的东西来好好的满足她早已湿润且骚痒的淫屄,使她达到性高潮,即使这个男人是我,阿姨也会淫乱的将大腿张开接纳我的手。但我却好像没打算让阿姨泄身,我只是重覆温柔地爱抚着阿姨的肉体,阿姨因迟迟等不到我的手指插入,而开始显得既着急又是难受,她不由得开始上下晃动着肥臀,好让贴在她臀沟里的手指有所反应,可是我就像是喜欢观看阿姨为强烈性欲所苦的模样的恶魔,我仍是继续的挑逗着阿姨,同时深埋在阿姨臀肉沟下的肉棒偶尔也会上下摩擦个一两次,但是就是不将我的手指插进阿姨的肉屄内,我要好好地欣赏阿姨那副为性欲着急而淫荡的样子,没多久,阿姨再也受不了我对她的性挑逗煎熬。
「拜托你……求求你……虾仔……给我……手指…我要……我要啊……鸣……手……」我听到阿姨几近哭泣地并摇晃着肥臀需求着我的手指不禁得意了起来。
此时我用食指与无名指分开阿姨的阴唇,把中指抵住阴道口缓慢的插了进去。我手指穿过大小阴唇插入温热湿滑滑的肉穴,方才抽插几下,期待已久奇痒钻心的肉穴立即产生一股妙不可言荡人心魄的快感,直涌上心头,传上玉首,袭遍四肢百骸。阿姨玲珑浮凸成熟而美丽的肉体由于有愉悦的快感而颤抖不已。阿姨那狭窄的阴道紧紧包围着我的中指,虽然阿姨不是处女,但里面还是很紧,可见已很久没用。
阿姨那久未被滋润的阴户,被我的手一摸揉已酥麻难当,再被我手指插进阴核,这是女人全身最敏感的地带,使她全身如触电似的,酥、麻、酸、痒、爽是五味俱全,那种美妙的滋味叫她难以形容。
「啊…啊…好……好棒…啊……啊!」阿姨轻轻的呻吟声急促不已,回荡在室内。
我又用右手大拇指头轻轻的揉搓着微微外翻肥厚紫红的大阴唇及细嫩绯红的小阴唇。间歇地将手指头插入小穴中抽插。不过大部分的时候她都是划圆圈的抚摩着珠圆小巧殷红的阴核,每一次指尖滑过阴核,阿姨平滑如玉的小腹都会收缩一下。我左手也没闲着,不断的玩弄挑逗着呀姨的丰满肉球。
我的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大,鲜红湿热的秘穴已经吐露出渴望的汁液,沾在指头上,大小阴唇上,闪亮着亮丽夺目的光芒。随着手指越插越快,力量也更加重些……阿姨口中发出的不只是呻吟,而是阵阵急促地喘息。
「虾仔────好美──好舒服────」
阿姨真是勾魂荡魄,使得我心摇神驰。此时经我一抚摸玩弄阴核,肉屄内立即不停流出大量的淫水。
我的手肏得阿姨浪声大叫:「啊,虾仔──我──我──我美死了,你的大拇指碰到我 的花心了──啊──。」阿姨的淫荡呻吟声也越来越大声,我的手则越肏越猛,淫水声「叭滋、叭滋」的响。插在阿姨小穴里的大拇指头,被扭动得感觉淫水越来越多,於是再将大拇指用力地抽插一下。
「阿姨!你舒服,是吗?一定要回答!」我得意的说。
阿姨娇羞叫道:「虾仔!不要这样嘛……不可以……」我笑嘻嘻的说:「阿姨!你的水流得浴缸都是了呢!这么多呵!」「……你别……别说了嘛!……!」阿姨羞得无地置容,结结巴巴的说。
我用大拇指顶住了呀姨的阴道口,却不急着插进去,这可让我难受极了,阿姨体内的欲望早已泛滥,我却还在慢悠悠的调情!特别是我那大拇指,已经把阿姨骚幽的缝儿撑开了一些,又热又硬,阿姨真恨不得马上把它整条吞进去才解馋呢!
阿姨强忍着性欲的饥渴,和我僵持了一会儿,只希望大拇指快点插入,但是,我那大拇指还是一动也不动,逗得阿姨下面又是一股浪水涌出!
阿姨忍不住了!快要疯了!忽然用力的把身体紧紧的贴上去,下体用力的向下一挺,只听见「噗!」的很响一声,我那大拇指就着住了阿姨泛滥的淫液,一捅到底!阿姨粉脸含春,媚眼半开半闭,娇声喘喘,浪声叫嚷 !
阿姨知道我在看自已出洋相,但是顾不了那么多了,阿姨太需要我那大拇指了!
我见阿姨已经主动求插了,也不再逗阿姨,大拇指在阿姨穴里上下抽插起来,弄出阵阵淫秽的「噗!噗!」的声音。阿姨淫水更加泛滥,泊泊的流出!
「呵!好……好爽!」阿姨闭目沈醉地叫春。
我的手指更快的插阿姨的小嫩穴,阿姨的屁股也摇晃的更厉害,头也不由自主的左右摇着,阿姨的长发早已淩乱的遮住了脸!我的手指抚弄玉乳及肉穴愈加用力,我更将大拇指留在肉穴外按压着阴蒂,其余四指皆插入阿姨的美穴中,奋力抽插不已,阿姨已经到最紧要的关头,阿姨芳口大张,忘情的叫喊。
「啊……虾仔……你的手……好厉害……摸得阿姨的……小穴……好舒服哦……啊……不要摸阿姨的乳头……它又被你摸的站起来了……好爽……」看着阿姨不断的被手指插入她的嫩穴里、又抽出的,淫水也越流越多,甚至是用滴的滴下来,连阴毛也多湿了!此时我用手握住大鸡巴对准阿姨的阴道,把大鸡巴抵在阿姨的裂缝上,准备插阿姨的小穴。
「啊……痛……痛啊……轻……慢一点……别动……虾仔……阿姨多年没插……没干过了,里面很紧……你要轻一点……」「啊……啊啊……好棒啊……虾仔……阿姨好美……好美……你干得阿姨好爽……阿姨好後悔……没有一早给你干了……」「啊……虾仔……阿姨爱死你了……嗯……干吧…阿姨就是……要你填满我的……小穴了……啊……小穴好美……啊……虾仔……你的肉棒好粗……好长……啊……顶到里面了……啊……你顶得阿姨好舒服……啊……啊……干吧……用力干阿姨……阿姨好喜欢你干我……」「阿姨,小浪穴呀姨,你的叫床声音让我好刺激喔!」「虾仔……你的…大屌……干得阿姨好爽……以後……阿姨……要你……天天……干我……虾仔……好好的……干……用力的……干……阿姨……的……浪穴……帮阿姨止痒……快……阿姨……爽死了……」我感觉我的血液快速往上冲,阿姨也察觉到我就快达到高潮,所以又加快速度的上下抽插着。
「……虾仔……快……给阿姨吧……射……到……阿姨……的体内……」我兴奋的说「阿姨,再快一点!让我们一起去吧!」阿姨听到我的话,更加卖力的上下起舞着。
「阿姨……我不行了!」
「虾仔!快给阿姨!一滴不剩的射向阿姨吧!」阿姨一声长叫,身体蹦紧,我随即放松,也同时射精,全射进了阿姨的小穴深处。
等到阿姨的阴道停止收缩以后,我才轻轻抽出阳具。只看见穴口顺着我的撤离而流出一丝一丝的黏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