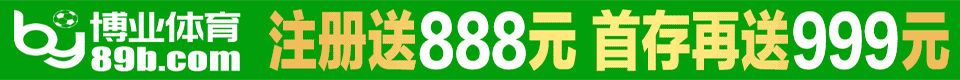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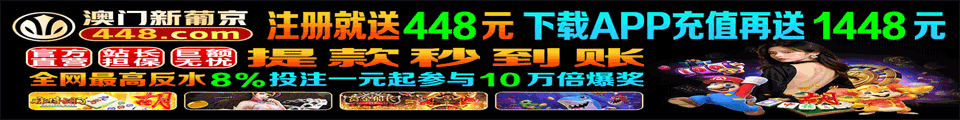


推荐观阅
友情推荐
【难知如阴续之侵略如火】(01-08)作者:fxb747
作者:fxb747
字数:30359
第01章
夏季落日的余晖洒满公园的树梢,归巢的鸟儿在天空盘旋,一阵微风吹过,
树叶摇曳闪着斑斓的光点。魏鹏牵着妻子走到自己的车旁,庄慧恋恋不舍的松开
手打开副驾驶,弯身坐了进去。
他却没有立即进入车里,而是有些稍稍愣神,漫无目的得目光随意望着远处
『三年了,带着那种心痛绕了地球一大圈,终于还是回来了。』『城市的味道还
是这么熟悉,我的亲人、爱人、朋友不知有没有变样?』『庄慧好像真的幡然醒
悟了……可是……她的眼神怎么那么的迷离……当我问起小宇的时候,她竟然躲
闪着不看我的眼睛……』『她现在是真爱了我吗?……』魏鹏心里闪现着种种的
念头,不过也就是闪现一下而已,然后自嘲般的翘了翘嘴角『有病啊?人真是贱,
得到了自己期望的目的了,还这么瞎想』打开车门弯腰进去,然后看着庄慧轻轻
的说道:『老婆,咱们先吃饭去吧?』『吃饭?哦……嗯,先吃饭去』庄慧好想
有些发呆,两只大眼睛望着车外,心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听到魏鹏的询问,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只是随口的应着。
她转过头来看着魏鹏有些羞涩的微笑道:『你刚回来,我们回家吃吧?我给
你做顿接风宴,欢迎老公的回归。』眼睑上还带着点点泪痕,长长的眼睫毛忽闪
着,并没有因为眼皮的红肿而失去以往的风情。
魏鹏伸出手轻轻的帮她擦去泪痕,很心疼的用嘴唇去去吻了一下庄慧的粉腮,
然后轻轻的把她揽紧怀里握紧老婆的手温柔的说道:『别回家做了,就咱们俩,
弄那么一桌子菜也吃不了多少,你就别忙活了,听我的。』『嗯,好吧,那我们
去哪里吃呀?你想吃什么,我请客,好好请你吃一顿,我们这么久没在一起吃饭
了』庄慧抬起头深情的望着自己朝思暮想的老公,一只手还紧紧地抓着魏鹏的衣
服,仿佛怕一撒手他就会消失一样。
『吃火锅去,南京路上的全顺居,在非洲这几年吃的那些烂饭,想起来就反
胃,做梦都想吃涮羊肉了,哈哈。』魏鹏大声笑着拍了拍庄慧小手,拧转着钥匙,
车子缓缓的开出了公园的门口。
来到全顺居,因为季节的缘故,饭点的时候人也不多。俩人进门在招待的引
导下上了二楼,要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庄慧乖巧的坐下后把招待递过来的菜单推
到魏鹏的面前,要魏鹏自己看着想吃什么就点什么。魏鹏也不客气点了四盘精品
肥羊,几盘海鲜,还有冻豆腐、粉条、腐竹、菠菜、白菜等辅助食材,因为人不
多上菜很快,不一会儿就摆满了桌子。
『先生,我们这里的羊宝不错,要不要来一盘,那可是好东西,今天半小时
前刚运来新鲜的哦。』脸上长着几颗青春痘的年轻小伙,又轻轻的走到桌子旁殷
勤的帮两位客人摆摆菜品,倒上茶水推荐着老板交代要卖出去的菜品。
『羊宝?哦……好……哦……不要了』魏鹏一听有新鲜羊宝,想到那东西的
功效刚想要一盘,可又想庄慧在一边,脸上难得的红起了脸,瞅了瞅女人就有些
不好意思的拒绝了。
『先生,这是我们店里的招牌菜哦,现杀现取,价格也不高一盘四个280
元,如果您觉得先前点了那么多吃不了我们可以退掉一些,而且我们还赠送大果
盘。』小伙听到男人想点,心里一阵高兴,老板交代过每推荐一盘就会提成40
%,可转瞬又听到男人的拒绝心里一阵失望又不甘心的继续推荐。
『来一盘吧,把羊肉退一盘,腐竹、粉条、豆腐不要了。』庄慧看了一眼魏
鹏转头对侍者吩咐道。
小年轻快速的在菜单上勾了一下,转身小碎步的走了,还带起一阵小凤,生
怕男人拒绝似的。魏鹏有点张目结舌的看了看远去的小年轻,又看了看老婆有些
嗔怪的说:『老婆,我不是说不要了嘛,这么多了也吃不了,你看你一说,这小
子转身就跑了,这么贵绝对有提成。不就是块肉吗吃不吃无所谓』『没事吃吧,
对男人来说是好东西……哦……不是……我是说……你刚回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呗,刚才你不是也想要点吗,三百两百的无所谓啦,看这招待这么殷勤』庄慧吞
吐的应声道着,脸上也起了红晕,掩饰般的看了一眼魏鹏,拿起一盘肉倒进了沸
腾的火锅里。还温柔的帮魏鹏把盘子摆好,酱料什么的都分好,做着一个妻子该
做的一切。魏鹏看着妻子的羞却模样心里一阵的温馨,以前的庄慧可是大小姐一
个,出来吃饭或者在家吃饭什么的可都是他在伺候着。
『三年没见了,我和她约定给彼此三年的冷静期,好好想一想,都留给彼此
思考的余地。看来时间真的会转变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啊』魏鹏深情的看着妻子
心里不无感慨的想到。
不一会儿侍者端着那盘新鲜的羊宝轻轻的放到桌子上,羊宝一个分了四瓣摆
出了四朵花的摸样,还有青菜点缀成枝干,很好看。魏鹏夹起两块放到锅里说随
便的说道:『在非洲三年竟吃些工作餐,偶尔的也有小灶,可是也都变了味道,
没有咱们这里的味道哦。非洲阳光好土壤好,可是哪里的人懒的要死压根就没有
几个种蔬菜的养殖的,还是我们自己种点蔬菜,养些猪羊,其他的都是冷库里面
的,没法吃。羊宝更没有这玩意稀少啊,一只羊才……哦……吃呀,竟听我说话
了,嘿嘿……』魏鹏觉得说羊宝有些那啥,就赶紧改口,他发现庄慧竟一直在看
着自己,眼睛里的柔情像要滴出来一样,让他心里一阵阵的悸动,有种想把女人
使劲抱在怀里疼爱一番的冲动。自己也是挺混蛋的,一走三年,扔下她一个人在
这个城市,岳父母也去了新西兰,女儿也不在她身边,儿子也上了国外军校。自
己心也挺狠的,可是那种情况下自己又能怎么样,那是唯一的办法了。其实也不
错现在看来当时的决定绝对是正确的。上官丽萍还一度质疑自己的这个决定,那
个女人……咳……咳咳……
见鬼了,刚想到上官丽萍,他竟然看到窗外楼下一个女人站在路灯下向他摆
了摆手转身走了,『是她?我操,不是吧?这女人阴魂不散啊,我这刚回来她怎
么也回来了,而且还跟踪我?』魏鹏想起在非洲建设码头,这个女人不时的到工
地『视察』,还专门找他单独汇报工作,多次暗示自己在汇报工作时可以更进一
步的『深入汇报』,可自己因为和庄慧的约定而忍了,不过忍得好辛苦好辛苦哦。
不由自主的脑子里想起那个女人的红唇、细腰,还有那双要人命的大腿,还
有那圆滚滚的奶子,还有那次在办公室汇报工作时,这个想让他就范的女人竟然
把玫红的内裤脱了下来,三角内裤上面竟然湿透了,丝丝连连的……
『想什么呢?快吃吧,都煮烂了』庄慧娇嗔的提醒愣神的魏鹏。
『嗯……想你呢……呵呵……羊宝好啊,我全吃了它,嘻嘻……』魏鹏一股
脑的把羊宝全倒进了锅里,沸腾的羊宝上下翻滚煞是好看。而自己的胯下竟然硬
了起来,一股想找女人做爱的冲动从心里『腾』的冒了出来,渴望,巨大想性交
的渴望不可抑制的映在脸上。
『啐,吃个羊宝你也不用这么猴急吧』庄慧娇嗔的说着,脸忽的通红,因为
此时她心里突然的想『羊宝是壮阳的东西,吃这么多会不会让他更很强壮……呸
……自己怎么会这么瞎想』庄慧说完用眼睛风情万种的瞄了一眼自己的男人,却
看到了男人耐人寻味的表情。
毕竟夫妻这么多年,她怎么会看不出此时男人脸上的表情,魏鹏眼睛里突然
出现的那种欲望,她不陌生,每次两人做爱之前,男人都是这种表情和眼神。每
次做爱时都是那么疯狂,自己的叫床的时候男人怕孩子们听到,总是用嘴堵住自
己的嘴,还故意的使劲抽插,他那么大的阳具抽插时都把自己都顶上天了。想到
这里突然庄慧感觉自己的两腿之间竟然流下了一股淫液。
『你……你先吃着我去趟洗手间』庄慧有些许慌张的站起来,把桌巾匆忙的
放下就离开了桌子。
魏鹏嘴里吃着食物连忙的嗯嗯这答应,看到妻子往洗手间方向疾走,心想,
此时的庄慧和以前还是一样做什么也没有个大家闺秀的模样,急匆匆,也不知道
淑女些。
庄慧今天穿着一件到膝盖的筒裙,肉色的丝质长袜,黑色高跟鞋,上身穿着
一件露肩吊带衫,走路的时候屁股扭得让魏鹏发颤,鸡巴硬了,硬的他真想现在
就把妻子按倒在地,撕烂她的裙子粗野的捅进她的阴户里,是的是捅而不是插。
打开卫生间的门,快步走进小隔间,庄慧撩起裙子看到淫水已经快淌出裙子
的遮盖范围,赶紧撸下丝袜的蕾丝边一直撸到膝盖,从旁边撕下一片卫生纸,从
下往上擦拭。
『哎呀,内裤也湿了一片,真是的怎么这么思春呀,也就是想了想而已』她
褪下紫色的三角内裤懊恼的又撕下旁边的卫生纸擦了擦内裤被淫水浸湿的区域,
又擦了擦自己的阴户『嗯……咝……怎么这么浪了?还在趟水哦,跟以前和小宇
做爱时一样,……小……宇……,不行……我不能再想他了,绝不可以我怎么又
想儿子了……』庄慧强行的止住自己的念头,懊恼的摇了摇头,将阴户和内裤清
洁干净,穿好后抹平丝袜,将手上黏黏的液体洗干净走出了卫生间。
随着就餐时间的加长,两人一边吃饭一边说笑渐入佳境,又找回了从前的感
觉,两人有说有笑,俨然就是一对多年夫妻在外面吃饭的模样,结账的时候魏鹏
刚要付账,却突然说了一句『老婆,埋单,你老公的钱都让你搜干净了』惹得妻
子在他胳膊上轻轻的捶了几下,然后两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先生,太太好幸福哦,你们俩真般配,让人看着羡慕哦』收银的小姑娘刚
才看到两人在吃饭的时候就那么的郎情妾意,现在有这么的温馨,不无羡慕的恭
维着。
第02章
两人离开全顺居,走进地下停车场,坐进车里以后庄慧突然的搂住魏鹏用嘴
胡乱的亲着他的脸,一边喃喃的说:『老公我们回家吧……我爱你……我……爱
你……今天我好高兴,感觉又回到了从前……呜……呜呜……』呢喃的话还没有
说完嘴巴就被丈夫用嘴堵住了,两条舌头缠绕这,互相的吮吸着。魏鹏捧着妻子
的脸使劲的湿吻着,恨不得把三年来的相思都找回来,车里只听到粗重的喘息声
和『啧啧……啧……啧……』接吻时发出的特有声音。
『嗯……嗯嗯……别……别在这里,我们……回家哦……』庄慧把丈夫的手
从两腿之间拽出来,喘着粗气的娇嗔道。
魏鹏嘿嘿一笑说:『走,咱们回家,嘿嘿……忍不住了,忍了三年了管子都
快爆裂了,哎嗂……别咬……咝……』原来妻子竟然一口咬在了他的胳膊上。
『你个没良心的坏蛋,我何尝不时为你守了这几年,我忍不住想咬死你,疼
吗?对不起』女人咬过以后又满怀歉意的用手抚摸着被咬的地方,心疼得问道。
『哈哈……没事,这才到哪里,你们看到我这几年都壮实了多少,虽然晒黑
了,可是浑身跟铁打的一样,咱们工人有力量嘛,咝……』魏鹏正咧咧着说,不
妨庄慧一把抓住了正昂首挺胸的胯下,小手隔着裤子一抓,过电般的感觉瞬间传
遍了他的全身。
『嗯,还行,壮实了啊』妻子恶作剧般的使劲用手攥了攥俏皮的说着,心里
却颤颤的想『好粗,好硬……真好……』『老公开车啦,路上慢些,快走啊!』
庄慧不舍得把手放开催促着魏鹏赶紧开车。
『到底是快开?还是慢开呀?这话说的』魏鹏一边启动着车子一边打趣的说
道。
换来的却是妻子一顿猛捶。
车子以最快的速度开回小区,开进进自家停车场,两人挽着胳膊亲热的走向
自己的家门,庄慧掏出钥匙打开门让魏鹏先进去,然后说自己还要把车上的行李
拿进来,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丈夫一把拉进了屋里『嘭』的一声单元门发出抗议一
般的闭上了。
住宅内也没有亮灯,只听到黑暗中传来悉悉索索脱衣服和男女粗重的喘息声。
男人探着头使劲的亲吻着女人,女人激烈的迎合着热吻,两只手却在解着男
人的腰带,因为激动得缘故,两只手竟然哆哆嗦嗦的使不上力气。男人双手已经
把女人的吊带粗野的脱了下来,一只手扯开了胸罩,两个雪白浑圆的乳房勃然爆
发了出来,男人两只手使劲的抓住揉搓起来。
『哦……啊啊……嗯嗯嗯……唔……唔唔……』女人嘴里含糊不清的呻吟着
使劲搂着男人的腰,想要把自己融化进男人的身体。
魏鹏弯腰一把抱起妻子用脚蹬开卧房的门,把妻子放到床上,转身走到窗前
拉上窗帘,打开了房间的吊灯。
『啊……坏蛋啊,要死啊,突然打开灯好刺眼哦』庄慧大呼小叫的喊着,因
为在黑暗中突然亮起刺眼的光芒有些不适应,下意识的拖过被角盖在了身上,还
用手捂住了眼睛。
『好老婆,让我看看,看看我朝思暮想的老婆,光着身子什么样我都忘记了,
哈哈,害什么羞呀,来给老公慢慢的脱,让我欣赏欣赏,你就馋死我得了』魏鹏
一边调侃着,一边脱下衬衫快速的脱下了自己的裤子。
庄慧在经过了短暂的适应后,又听到魏鹏的调侃,慢慢掀起被子,满脸桃花
的笑着,竟然伸出鲜红的小舌头挑逗般舔了一圈嘴唇,抬起屁股脱下裙子,慢慢
的往下撸丝袜一边脱丝袜一边淫荡的扭动着身子,两个硕大的乳房甩来甩去,还
是那么坚挺,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干瘪和下垂,两粒奶头坚硬的挺立起来,
随着奶子的摇晃而画出重叠的光晕。
脱下丝袜后又抬起屁股把三角内裤从一条腿上褪出来,就那样挂在另一条腿
上,还慢慢的把两条腿伸出床沿,穿上了床下的高跟鞋。
身子往后躺下把两条腿摆成成『M』型,高跟鞋蹬在床沿上,顿时黑黝黝阴
埠呈现在魏鹏眼前,还有那已经淫水泛滥的阴户,湿答答把生殖器一周的阴毛都
浸湿了一片。
女人一只手搓揉着奶子,一只手撕扯着自己的阴唇,不时的用中指在阴道口
抹些黏液涂到已经肿胀的肉粒上,涂得时候身子不由自主的一颤一颤,嘴里遂即
咿咿呀呀的呻吟着。
魏鹏用手撸着自己的生殖器,感觉到手里的鸡巴火热滚烫,自己的身子也火
热滚烫,自己的心里也火热滚烫,眼前的妻子才是自己的女人,结婚这么多年她
从来没在插入以前对自己做出这么淫荡的姿势,都是两人战斗进入酣畅的时候才
疯狂的大叫和玩各种的姿势。她现在这个样子,曾经在自己偷窥女人和儿子偷情
的时候才见过。
脑海里闪现着庄慧和魏宇母子乱伦是的场景,让魏鹏感觉到了一种变态的快
感,竟然爽的身体从心里到身体都有些发颤,『我怎么这么黑暗了?怎么想起了
乱伦,难道我的内心还存在着变态的黑暗吗?』『老公……来……啊……老公…
…来……啊……老公……』妻子扭动着身体,嘴里呻吟的哀求着,两条雪白的大
腿使劲的往外张着,因为穿着高跟鞋原因两只脚变成了一种夸张的形状,但是却
显示出一种很淫荡的张力,阴道口的两片唇瓣已经充血,随着阴道的收缩一张一
翕,黏黏涟涟的液体顺着股沟流到床单上,湿了一片。
听到妻子呻吟中的哀求,魏鹏脑袋嗡一下,血脉贲张!!压制已久的欲火再
也控制不住了,他快步走上前去对准阴道口,没有什么前奏,就使劲的狠狠捅了
进去『噗哧』全根浸没,阳具就像陷入了沼泽的泥泞一般,湿滑还有一股吸力,
很紧。因为鸡巴的进入,把里面的液体挤了出来,一股热浪打湿了他的阴毛,然
后顺着两个阴囊滴滴答答的流到了地上。
『啊啊……啊哦……死人啊……太大了……咝咝……啊……啊……进来了…
…啊哈……啊……』女人因为男人阳具深深的插入而使劲夸张的长着嘴,喉咙里
断断续续的说着连不成句子的单字,眼睛一个劲的泛着白眼,使劲的摇着头甩着
头发,此时女人的感觉就是『爽、饱满、快感和阴道满满的充实感。』庄慧使劲
的喘了口气两只胳膊探出伸到男人的后臀上,脖子硬埂着抬起来,用嘴在男人胸
前胡乱的拱着伸出舌头乱舔一气,找到了男人的乳头一口吸住,两只手使劲的扒
着男人的屁股,阴户卖力的往前顶,就像是要把男人整个的按倒自己的身体里一
样。
肿胀的阴蒂在这种急迫的压迫和摩擦中一股晕眩的感觉传满了女人的全身,
庄慧用牙齿咬住老公的乳头嘴里哼哼唧唧,头嗡嗡响着飞上了天。一阵高潮的晕
眩传遍了每一个细胞『嗯嗯……嗯嗯……』的哼了两声竟然第一次高潮来临了。
魏鹏使劲的插入以后正在感受插入瞬间的快感,还没有抽插,就觉得女人阴
道壁一阵阵的收缩,子宫口来回的磨着龟头,一股吸力从阴道深处传来,让他想
起了与崔莹性交时,那种阴道里特有的吸力,而胸前的一个乳头被女人吸在嘴里,
舌头转着圈挑逗着让他快感连连酥麻难忍,突然女人用牙齿咬住了乳头,下面交
合处一股热浪涌了出来,烫的魏鹏腰眼酥麻,想射精的感觉涌上脑袋,他一下抽
出阳具,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气,想压住这股快意。
『啊……啊啊啊……哈……啊……爽……老公……好爽……插我……』因为
阳具的突然抽出,阴道里一阵的空虚,庄慧着急的用手抓着魏鹏的鸡巴一个劲的
往前凑,嘴里还呻吟着哀求连连。
『呼……想要老公的大鸡巴吗?唵……说呀……想不想……爽不爽……大不
大……』魏鹏此时大男人的虚荣心极度膨胀,不过他的确是有骄傲的本钱。
『大……好大……好硬……好老公……快……快干我……』庄慧一只手抓着
坚硬的鸡巴,一只手食指快速旋转摩擦着着自己的阴蒂,一勾一勾的逗弄着,身
体随着手指碰触阴蒂而一次次颤抖,延续着快感。
确定自己已经把要射精的快意压下后,魏鹏深吸一口气又缓缓的对着女人的
阴道插了进去,然后快速抽出再深深插入做着机械的打桩动作。
『啊……哦……哦哦哦……嗯嗯……啊……嗯……啊哈……啊哈……啊……
啊啊……嗯嗯……』随着阳具的抽插,庄慧嘴里不停的大声叫着,淫荡的样子溢
满眼睑,阴道壁和阳具的摩擦让她满足的快感连连。
身下女人淫靡的表情和不断升高的叫床声刺激的魏鹏更加快速的抽插起来,
啪啪啪……啪啪……的声音越来越频繁。庄慧觉得好兴奋好刺激,兴奋的用手使
劲的搓揉着自己的乳房,穿着高跟鞋的两只脚上下的摇晃着,一条腿上的内裤象
一面淫荡的旗帜来回的飘摇,更让魏鹏淫性大发。
因为男人加大了抽擦的速度和力量,让庄慧感到了前所未有刺激感觉,就像
释放了埋在心里的淫魔一样大声的叫了起来,阵阵快感如潮水般涌上庄慧的心头,
让她的身体一阵阵的僵直,奶子被揉搓的通红,一道道的红印横七竖八的交错着。
第二次高潮的来临,让庄慧满足的颤栗不已,那种感觉就是立马死掉都甘心,
而魏鹏却越战越勇,当妻子高潮到了的时候,他突然冒出了王瑶曾说过庄慧就是
一个『婊子』,脑海里竟然出现了王瑶描绘魏宇从后面象街上的操狗一样从后面
插入庄慧阴道的画面『操死你个婊子,老子的鸡巴比儿子的大多了,操死你这个
烂婊子,我要从后面操你……』魏鹏的心里不断的这样大喊,让他更加的性奋不
已。
今晚妻子淫荡的配合让他性趣高涨到了临点,把妻子抱到床下,让她扶着梳
妆台的边沿站好,用手劈开两条白花花的大腿,女人翘起屁股,阴户大开,白浆
一股股的往外冒着,顺着大腿流到脚上蹬着的黑色高跟鞋上,配合着此情此景,
白色和黑色形成了醒目的淫荡气息,还有一只脚上套着落下来的内裤更刺激着他
的欲望大涨。
第03章
庄慧半趴在梳妆台上,两只浑圆的奶子倒垂着,奶头似碰不碰的扫荡着台面,
长发因为之前的摇甩而散乱不堪。她回过头如丝的媚眼看着男人,小舌头舔了舔
嘴唇,然后咬着下嘴唇,做出一种特别淫荡的表情,抬起一只脚小腿后弯着用细
高跟碰了碰那昂首的阳具,摇了摇屁股,然后使劲撅了起来,以一种淫荡的姿势
等待着男人的插入。
魏鹏上前一只手扶住女人的细腰,一只手抓着生殖器的龟头套弄了两下,然
后在湿答答的阴户上来回的蹭着。
『快……亲亲老公……快进来……别折磨我了……插我插我……干我吧……
亲老公哦……』女人摇晃着屁股用阴户磨着坚硬的阳具哀求着。
『噗哧……』『哦……啊……啊啊哦……真好……干我……干死我……哦啊
哦……嘶……嗯嗯……哦嘶哦嘶……啊啊……』庄慧已经进入了一种高度兴奋的
状态,全身泛着一种病态的红色,渴望着被征服的性冲动不断的冲击着她的心房。
『来啊……老公……快……快进来……我是你的……要我要我……来嘛老公
……摸我的阴蒂……痒……痒啊……来啊干我……快快……打我……哦……对…
…对……打啊……打啊……打死我……爽……真爽……』妻子哀怨的要求让男人
更加的兴奋,阳具在阴道里面的抽插变得更加快速和粗暴,魏鹏用手『啪啪』的
打着庄慧雪白的屁股,两臀瓣还因为大手的拍击出现一层层的韵浪,乳白色的淫
液一股股的喷射在男人的阴毛上,在交合处混合成白色的泡沫『咕唧咕唧』的性
交声音快速的在卧室里回响。
女人现在已经没有了力气,将身体直接趴在桌面上,浑圆的乳房被挤压的变
了形状,往身体两边涌出,女人死命抓住桌沿的一只手骨节已经发白,另一只手
却伸到自己的两腿之间使劲的搓揉着肿胀的阴蒂,泡沫状的液体随着女人的小手
指尖滴滴答答的拉着丝落在地上,嘴里已经发不出声音,只是……呵……呵……
的配合着阳具快速的抽插从喉咙里挤出断断续续的呻吟。
魏鹏一边快速抽插一边用拇指蘸着黏黏的淫液在庄慧的肛门上研磨,不时的
还把拇指捅入庄慧的屁眼里,刺激着妻子的快感,女人抗议般的扭动着身子,似
乎有些不舒服,但是拇指已经全部捅入,在肛门里旋转着,当拇指不断摩擦大肠
膜壁时快感一阵阵来临了,庄慧已经发不出声音的嘴巴随着阵阵的酥痒,头颅高
高昂起,嘴巴张开大大的『〇』着,感觉自己又一次飞上云端。
不间断的抽插了将近二十分钟,一阵刺激的快意来临,魏鹏精关大开,他猛
的一下从已经被白色淫液覆盖的阴道中抽生殖器大喊道『快……快……嘴……嘴
……』『呜……呜……嗯嗯……咳咳……嗯嗯……嗯……』女人快速的转过身蹲
下来,一只手扶男人的臀部,含住伸到嘴里的阳具,滚热的液体喷薄而出,她快
速的用嘴套弄着,咽喉不断的滚动吞咽黏稠的精液,另一只手却快速的伸到自己
生殖器上飞速的上下摩擦,竟然在这次高潮的末尾又来临了一次,淫水和大量的
尿液一起喷薄而出,撒了一地,竟然最后潮喷了。
王瑶说过庄慧在极度兴奋的高潮时会撒尿,看来这次的性交对庄慧的刺激不
小,竟然咝咝的撒了一地。
『婊子』一词再次闪现在魏鹏的脑海里,儿子和母亲乱伦的画面不断的闪现
在眼前,让他继续产生着莫名的性冲动,『也许男人都有这种病态的嗜好,越是
不符合常理的伦常越是能刺激男人阴暗的兽性吧?是不是应该自责呢?谁知道,
去他妈的我本来也不是个正人君子』他在心里一边自责自己的变态一边又为自己
开脱着。
妻子『吸溜……吸溜……』的舔舐着满是精液的龟头,女人闭着眼睛卖力的
用舌头舔舐剩余的精液,很享受的淫靡表情映在脸上,而另一只手还在撕扯自己
的阴唇,食指不时的插入阴道,手上的淫液和尿液因为摩擦而发出咕叽咕叽的响
声。
暴怒的阳具并没有因为射精而软榻下来,还昂怒着宣示自己的健硕,套弄着
阳具的小嘴被撑的有些变形,鲜红的嘴唇随着套弄阳具的动作而出现阵阵白色,
残留在嘴角的精液与鲜红嘴唇形成了醒目的淫荡气息,魏鹏很享受的嘴里发出了
『嘶嘶』的声音。
『啵……它怎么还这么硬呀,被你弄死了啦,怎么还不软呀……累死了啦…
…』女人吐出依旧坚硬的阳具,舔干净最后一滴精液。用湿湿的小手拍了一下老
公的屁股,娇嗔柔弱的责怪着。
『真的不行了,自己真的没有力气了,太强壮了,怎么感觉比以前更大更粗
了,弄得人家都尿了,丢死人了。』女人心里一阵的莫名的念头涌上心头,有羞
愧有期待,但是羞愧的同时心里还是充满着满足,女人就是这样,当被一个男人
征服了身体的时候,她就没有了自我,只想用自己的身体去再次的讨好这个征服
者。
『老婆……老婆大人……你看它还没有软啊……憋了三年啊……走走后门吧
……嘿嘿』魏鹏献媚的讨好道。
『不要呀……没力气了……真不行了……呜……啊……要死了……疼疼……
嘶……嘶……呼……呼……』魏鹏却不理妻子的拒绝,一把抓住女人的头发把她
翻转过来,按倒梳妆台上粗暴的将阳具插入了女人的肛门,女人大声的喊着咝咝
的抽着凉气,屁股还急剧的扭动,想要脱离阳具的侵入。
因为有淫液和尿液的润滑加上刚才拇指前期的开拓,阳具没有阻碍的插入了,
魏鹏并没有急着抽插,而是抱着女人的身体趴在她的背上,轻轻的舔着丝绸般的
脊梁,用手抓着两个通红的奶子揉搓着,所以女人也慢慢的安静下来,只是咬着
牙嘶嘶的抽着凉气哼哼哼的抗议着,诉说自己的不满。
『没事……不疼……乖……别动……让老公疼你……乖啦……我慢慢的哦…
…你看镜子里这样的姿势多淫荡……像不像街上的操狗……』魏鹏一边安慰着妻
子一边用舌头在女人的背上游走,用舌头舔着庄慧的耳垂轻声的挑逗着女人的感
官。
庄慧抬起头看到镜子里面充面淫荡样子的脸,有些恍惚起来,记得儿子也喜
欢这么操自己,喜欢从后面干她的屁眼,而且在干之前也是舔她的背,嘴里还妈
妈妈妈的叫着,喜欢的不得了,说最喜欢从后面干妈妈的屁眼。
随着念头的涌起,庄慧的阴道一阵收缩大量的淫液又不可抑制的淌了出来,
顺着雪白笔直性感的大腿流下去。魏鹏感觉到身下女人竟然有些轻轻的痉挛,从
大肠壁传来阵阵的收缩,而且还能感到女人阴道也在收缩,还发出『哱哱』的响
声,魏鹏脑子里出现了两个字『尤物』!!
每次和岳母做爱的时候他也赞美岳母是个尤物,没想到母女两都是尤物,各
有千秋,各不相同『真他妈爽,母女都这么浪,哈哈』他心中一种狂妄的满足感
急剧膨胀起来,可他却不知道女人为什么突然这么兴奋。
『嗯嗯……好了……干我吧老公……干我……啊啊……咝咝……』庄慧看着
镜子里的老公竟然恍惚的和儿子的影子重叠了起来,莫名的兴奋让她哀求着男人
快干她,随着阳具慢慢的抽出插入,庄慧脑子进入了一种虚幻的景象『儿子在她
后面趴在她的背上,妈妈妈妈的叫着,抓着她的奶子,使劲的用生殖器在操她的
屁眼』『干我的屁眼吧……啊啊……哦……哦……抓我的奶子……我的奶子好不
好……快干我……使劲干……我……我喜欢你……干我屁眼……小老……嗯嗯…
…哦……啊啊干我……老公干我啊……使劲……啊啊……啊啊……』女人眯着媚
眼嘴里叫床声不断,差点喊出小老公时用哼哼的呻吟声掩饰了过去。
魏鹏此时只顾着感受鸡巴被肛门紧紧环箍的那种感觉,享受着阳具和大肠壁
摩擦的快感,并没有听清女人呻吟的叫喊着什么。卖力的又抽插了二十多分钟,
一泻如注再次射精了,射进了妻子的肛门里,抽出阳具时浓浓的精液咕咕的往外
冒着,庄慧转过身温柔的把已经服软的生殖器含在嘴里轻轻的舔干净,然后用舌
尖碰了碰龟头娇喘着嗔嗔的说『坏东西……差点把我弄死……老公抱我去洗澡啦
……累死了……真的没力气了』两口子清洁完身体,也不管地上的一片狼藉,魏
鹏把妻子从浴室横抱到床上,不顾女人的阻挠和哀求再次提枪上马。
只听到卧室里传出女人疯狂的喊叫,沉寂了一会儿又传出了啪啪打屁股的声
音和女人高声的叫床声,声音再次沉寂以后,不一会儿又响起女人的喊叫声,如
此反反复复,让庄慧连续的来了多次高潮,最后女人彻底进入了生理假死状态,
嘴巴大张着,眼睛翻着白眼,浑身僵直任男人在自己身上征伐,当魏鹏满足的趴
在妻子身上时,女人慢慢活了过来喘着粗气眼睛呆呆的望着天花板说了一句:
『你不是人,你是头驴……』只好再去浴室洗一次,最后双双躺到了床上,妻子
温顺的从旁边烟盒里抽出一支烟送到丈夫的嘴里,欠身拿起火机给男人点上,把
烟灰缸放倒了男人的胸膛上。
『咝……爽啊,老婆,你以前可是不喜欢我在家里抽烟哦,完事后我抽烟你
也不喜欢,你老公有点受宠若惊,哈哈』魏鹏惬意的吸了一口,美美的说着。
庄慧用手轻轻的捶了两下老公的肚子,顺从的趴在男人的臂弯里像只小猫一
样眯着眼睛很享受的轻轻说道:『时间会改变一个人的习惯和理念,脸上的伤好
了以后,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独自上班下班,那种孤独一度的让我崩溃,我曾
经想到了就是了却此生也不要这样一个人孤零零活着,可我一想到你还在盼着我
念着我,我们还有女儿还有……儿……子,还有我的父母,你的那一大家人呢,
我就坚强的这么过着一个人的生活……啜……啜……我知道……啜……啜……我
以前错了……对不起老公……我爱你……啜……啜……』女人说着说着轻轻的抽
泣了起来,睁开眼睛抬起头委屈的望着男人,眼睛里的幽怨要多深有多深。
第04章
『好了,好了,都过去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嘛,我如果不爱你我能把自己自
我放逐吗,说起来以前也不都是你的错,算了不说了。让我看看你的脸,周鲲那
小子找的这个南*棒南傍国医术还不错,呵呵,看不出疤痕哦,我今天回来的时候去
所里找他,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熊抱,哈哈,所里换了好多人,好多不认识了,
我本来想开我的车来着,他竟然把我以前的车卖了,还说那破车档次太低,给我
买了一辆辉腾,跟帕萨特似的,不过挺好,哈哈……』魏鹏看了看妻子的脸,那
道伤疤已经看不出丁点的痕迹,可是时间就像在她这里停住了一样,皮肤还是那
么吹弹可破,还是那么水嫩,一点也不像两个孩子妈妈的样子。
『对了,我不在的这三年,周鲲有没有照顾过你,不过我量他也不敢不照顾,
哈哈,只要别照顾到床上就行,哈哈……哎哟,别拧我……疼疼……嘶……嘶…
…』魏鹏心情大好的调侃着妻子,当他说到后面时庄慧一把拧住他的乳头狠狠的
转了个圈。
『胡说什么呀?一个是你铁哥们,一个是你老婆,再瞎说我不理你了』庄慧
生气的转了个身背对着老公,很生气说着。
魏鹏慌忙掐掉香烟,把烟灰缸放到床头上,讨好的从后面搂住妻子轻声的道
着歉:『好老婆,老婆大人别生气,逗你玩呢,啊哈哈,好了我不对,我道歉,
以后不开这样的玩笑了哈,别生气了,来,老公抱抱』庄慧顺从的转过身趴在老
公的怀里,用手紧紧的搂住魏鹏,把头贴在坚实的胸膛上,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说:
『嗯,真好,在你怀里真踏实』她的眼睛忽闪了几下,目光里却闪现了一丝慌张,
转瞬即逝!
随后几天魏鹏没有急着去事务所,而是陪着庄慧去江南小镇玩了几天权当散
散心,给妻子买了好多衣服鞋子首饰之类的东西,就当是补偿这几年的亏欠吧。
以前自己陪妻子的时间的确少,虽然基本每天晚上回家睡觉,但是真像这样
陪妻子逛街购物玩耍几乎没有过,结婚以后都是庄慧带小孩,魏鹏则是跑案子做
代理。庄慧忙了就把孩子送岳母家,闲时一个人带,小雯出生以后两人更是忙碌
了起来,夫妻间的激情随着锅碗瓢盆慢慢消磨殆尽,有的也只是亲情,维持一个
家庭完整的亲情。
庄慧在这些天里表现的很温柔,百依百顺一副小鸟依人的小女人样子,可以
看出对魏鹏的依恋和眷恋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丝的的做作和伪装。幸福的样子
溢于言表,每天都带着甜甜的微笑嘴里也是『亲爱的……亲爱的』喊个不停,两
人就像热恋中一样的甜蜜。
魏鹏有些恍惚,仿佛以前发生的一切都是虚幻,现在才是真实的,被人依靠,
眷恋,让他感到了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的荣誉感,满足感和责任感。
过去,他觉得那是一种麻烦,他觉一个美满的家庭,就是自己主外赚钱女人
主内持家,要有独立的自我,而不是一种依赖般的拖累。所以他找女人,只找那
些不会给自己带来太多麻烦的女人。
其实得到一个女人的爱,对男人而言,或者远比事业和金钱更能让男性满足!
魏鹏现在就是这种心理状态,他甚至不想再去事务所了,抛开一切就这样跟妻子
到处去旅游到处去玩耍,享受着甜蜜的二人世界,不再去勾心斗角的与外人争斗。
可是,是人就离不开现实,离不开金钱,还有地位和争斗,理想都是很丰满
的,现实总是很骨感,周坤一个电话把魏鹏有拉回了现实中。
『大鹏,咱不带这样的啊,回来十来天了,你跑哪去了?事务所你不要啦,
我他妈一个人都快得心劳猝死啦,你还管不管啊?还有好多事我要跟你商量呢,
你他妈拍拍屁股一走三年,回来后打电话跟我说事情都解决了不是吗?麻利的给
我滚回来……』『……』魏鹏只有苦笑的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家伙。
『我这正和庄慧在外地呢……我立马买飞机票回家……明天……明天就滚到
你面前……哈哈』魏鹏挂上电话和妻子说明了情况,庄慧很善解人意的收拾行李
箱,俩人结账后直奔飞机场。
下午两人就回到了家,两口子亲密的一起去买了好多菜,魏鹏亲自下厨操刀,
庄慧打帮手,做了一桌子丰盛的烛光晚餐,美美的过了一个二人世界,晚上又颠
鸾倒凤的盘肠大战了一番。
早晨的太阳一出来就称职的挥发出阵阵的酷热,并没有因为是早上而有所收
敛。阳光白炽炽的有些刺眼,晨练的老人已经锻炼完毕,有的提着剑、有的拿着
舞扇、有的提着鸟笼、断断续续的往家走,有些买了早点回家要叫儿孙们起床吃
早饭上班上学。
魏鹏慢慢的睁开眼睛,摸摸索索的打开手机看了看时间才六点四十,扭头看
看了看旁边还在酣睡的妻子,只见庄慧弯曲着身体侧躺在一边,一副很秀气的睡
姿,头发撒落在枕头上,两只胳膊好看的搭在一起,滚圆的乳房随着呼吸颤颤的
一起一落,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做梦,女人长长的睫毛不时的抖动一下,诱人的樱
桃小嘴轻轻抿住,有些微微的撅着。
『庄慧也就在睡觉的时候还有些大家闺秀的样子,这么一张小嘴巴含着我的
小弟还真是挺舒服,昨晚真够疯狂的……小别胜新婚,这一别三年回来夜夜是新
郎啊。』看到妻子诱人的樱桃小口,魏鹏龌龊的在心里想着。
伸手理了理女人的乱发,欠起身吻了一下妻子的额头,心里充满满足感,觉
得生活终于回到了正轨,自己也回来了,妻子的身心都转到了自己身上,以前的
那些都随着时间逝去了,过去了也就过去了,魏鹏不是个拿不起放不下的人,从
知道妻子的事情到现在他所做的种种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稳住曾经温馨的四口
之家,他的『阵地』。
妻子轻轻的翻了个身,拉起被角盖在身上,嘴里迷糊的嘟囔着『别闹……让
我再睡一会儿……累……』出门之前魏鹏给妻子留了张纸条,说自己今天去事务
所里肯定要喝酒,晚上不一定早回家,早饭让她自己弄点吃,如果今天累就别上
班了等等等等。
在快餐店吃完早饭,开车来到了事务所,站在楼下,魏鹏抬头看着楼顶上鲜
红的『鲲鹏律师事务所』这几个字时眼睛有些湿润,这个事务所就像自己的孩子,
从无到有都是靠他和周鲲的打拼才有今天的规模,自己因为家庭的变故一走了之,
还好有周鲲这个生死兄弟在,才没有让事务所余晖日下啊……
正在他感慨的时候,一个人慢慢的走到他的身后『大鹏,是不是看着这几个
字特有感情,呵呵,我每次下班上班都要看一眼,这是你和我的骄傲啊』周鲲也
抬着头看着这几个字幽幽的说着『你回来就好了,我一个人还真吃不消,案子多
得接不过来,我又套上了这么狗屁区人大代表,今天会议明天会议,他妈的,还
焦头烂额啊』魏鹏听身后在说话转过身双手抓住周鲲的两只胳膊说道『你个大混
球,不是特厌恶官场?不是想着移民美帝国主义去拯救那里的人民,那里的姐妹
于水火之中吗?哈哈,你小子隐藏的很深啊,都代表人民了哈行啊,我这个小民
是不是以后还要仰仗你这个官老爷过活啊』『好了好了,别扯淡了,走吧魏大律
师,该你回来行事你的职业操守了啊,美帝国主义的姐妹再说啦,你这拍拍腚走
了,我可累的跟孙子似的,别这么幽怨的抓着我好不好,让别人看见还以为我怎
么着你了一样,咱俩别来感激啊什么的那一套,走吧……』周鲲故意做出敬而远
之的样子,嘴里嚷嚷着,但是脸上却掩饰不住兴高采烈的表情。
魏鹏的办公室一直留着,每天都有人打扫,还是那么整洁明亮,魏鹏坐在自
己办公桌的椅子上,望着屋子里的一切有些发呆,鼻子里呼吸着办公室特有的气
息一时感慨万千。
周鲲不一会儿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叠表格,走到桌子旁轻轻放下眼睛盯着
魏鹏神秘的说:『这是咱们事务所的财务报表,不动产和资金情况,总资产都在
这里,你看看吧,你走的时候说要走三年,把事务所交给我,还说这三年的收入
全归我,你看看这三年我赚了多少?你亏大了,你个傻逼!』魏鹏拿起来认真的
一页页的看着当看到总额时吓了一跳,竟然总资产到了1。8个亿,我操,怎么
这么多?当他看到资产分配表格时慢慢的站了起来,认真的看着周鲲的眼睛严肃
的说道:『你确定是这样的分配吗?你觉得这样可以吗?我不同意!!』周鲲拍
了拍表格说:『就这样分配的,你同意不同意就这样了,你屁的不同意,晚上全
所一起聚餐,你先看看吧,一会儿姜小玉来了再向你汇报现在的业务,妈的,我
还要去区政府开会』说完转身就要离去。
『谢谢……』魏鹏没有坐下而是看着周鲲转身要走呐呐的说道。
周鲲打开办公室门的手僵了一下,头也没回用另一只手在空中挑出一个中指
说了句『有病啊』。
事务所在这三年里竟然利用官司的漏洞收购了几个在繁华街道店面,还有一
个物流公司,另外还兼并了区里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而资产的分配
竟然是他和周鲲平分各占百分之五十。
资产的激增让魏鹏很激动,没想到这三年竟然有这样的大收入,而周鲲的资
产分配又让魏鹏很感激,自己走得时候事务所才一千多万的资产,一切都不用多
说了生意搭档的态度让他那种生死知己的感觉油然而生。
八点一刻,事务所热闹了起来,原先四五十人现在已经两百多人了,一到了
上班时间大厅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有咨询的、有办案的、有正在跟代理律师组
织材料准备出庭的,满大厅嗡嗡的好不热闹。
姜小玉抱着一摞文件袋走进办公室,一脸兴奋的嚷道:『鹏哥,你回来就好
了,这几年鲲哥忙得一个头两个大,哈哈,这一大摞我们代理的刑事案子,不过
法院公诉律师的代理不多就这几个,你看看,鲲哥走得时候说大家晚上聚餐,嘻
嘻……,去哪里吃啊?』放下这一大摞文件袋,分门别类的交代好后姜小玉笑嘻
嘻的问着魏鹏。
魏鹏说自己也有几年没回来了,就问姜小玉现在有什么好的档次高的场所没
有,并且豪气的说,哪里贵就去哪里,姜小玉说去年在屏东路新开路一家五星级
酒店,吃饭档次是很高不过就是没有什么娱乐,怕所里的男同事不同意去,魏鹏
只是说老规矩就是了,姜小玉哈哈一笑知道该怎么做了,所谓的老规矩就是吃完
再找好的娱乐场所就是啦!
至于娱乐场所当然是去卢永祥那里了。魏鹏找出卢永祥的电话,接通后电话
里卢永祥很意外,多年不联系的魏鹏怎么给自己打电话了,一口一个鹏哥的叫着
说自己的汽修厂已经卖了,开了个4S店明面上主营国产汽车,内地里是搞汽车
走私,KTV早换了地方了在沙滨大道,叫好迪乐量贩式KTV,很新潮的名字。
魏鹏告诉卢永祥晚上要包场,让他安排一下,卢永祥满口答应下来。两人敲
定了时间后互相说了些没有营养的话挂了电话。
下午周鲲回到事务所跟魏鹏在办公室里详细的解说这三年是怎么赚到这些钱
后,让魏鹏恍然大悟。
『冯建国』现任第一副市长,市委常委,主管司法和城市建设,今年主要负
责新区建设。也就是在魏鹏离开国内的那年,从南方省调往本市任职,他的岳父
就是张扬旗,魏鹏岳父的同窗好友,因反革命罪蹲过监狱,后来岳父曾多方打听
也没有找到。
张扬旗因为『XXX事件』与周恩来顶撞被高层认定为反革命,被指为吴法
宪的狗腿子,阻碍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反派,认定与当时被的『XX副主席』一个
集团,先是被摘了官帽,然后因为某件事被打倒,70年被判处枪决。可是魏鹏
在一次办案的过程中查到一份76年的判决书,上面说张扬旗被法院判处了二十
年的有期徒刑,之后就音讯全无了。
周鲲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到冯建国,两人在一次酒会上偶尔的说起来,才知
道张扬旗依然健在身体很健康,现住在琼崖省的泉水市。周鲲知道后说出魏鹏岳
父的名字,说自己是魏鹏岳父的干儿子,并说老人已经找寻了张扬旗十几年。冯
建国给岳父打了个电话求证后让周鲲跟岳父通了电话。
第05章
张扬旗在电话里很激动,一度表示要来本市找昔年的好友一聚,可当听说老
友已经在新西兰定居时甚是失望,在电话那头扼腕痛惜与老友的失之交臂,并嘱
咐冯建国尽全力照顾周鲲,力所能及的给于帮助。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冯建国利用职务之便给鲲鹏律师事务所最大的便利,
还劝导周鲲参政挣选区人大代表。短短三年就让事务所的业务扩大了数倍还顺便
的收购了一些不动产。当然在这三年里冯建国也不是无偿的帮助,周鲲这样八面
玲珑的人物事体做的乒乓响,很上道的对冯建国『意思』了好多次。
魏鹏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心里酝酿出来,拍着周鲲的
肩膀笑意盈盈的说道:『活该咱们哥们发财,这么好的关系不用是傻子,哈哈,
我听说玉东有大动作,咱们哥们好好弄一回怎么样?』周鲲有些不解的看着魏鹏
迷惑的问道:『什么意思?』『啥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今年那边有几十个镇合并,
成立新区,里面我们可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啊,闲置土地会很多,那都是钱啊』
魏鹏神秘兮兮的说道。
玉东今年要成立新区撤镇合并的消息还是在回国之前听到上官丽萍说的,这
个女人消息的灵通到了惊人的地步,高层的一些动向和决策她都能打听的到,毕
竟有这么个家族背景在,各种消息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上官丽萍的耳朵里。
当时魏鹏听到后也没觉得有自己什么事,事务所的资产满打满算也就一千多
万,扔进去也打不起水花,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账面闲置资金就有七八千万,还
有冯建国这么好的一个后台,想不赚钱都难啊。
魏鹏只是告诉了周鲲自己的一些粗略想法,但是怎么利用人脉这件事上两人
一拍即合,两人在兴奋中敲定了一些细节,事务所的事情还是周鲲挑大头,跟冯
建国的接触换成魏鹏,另外魏鹏要在之后的日子里多跑跑新区找项目,看看哪里
可以下手。不知不觉中快到下班时间了,周鲲最后拍了拍魏鹏的肩膀说:『大鹏
你说的这些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具体我不是很熟悉,毕竟你在学法律之前读过两
年经济学,我被你说的头都快涨破了,只要赚钱你就去搞,赚了是咱俩的,赔了
也是咱俩的,我支持你,大不了咱俩从头来过嘛』两人在嘿嘿的奸笑中结束了密
谈。
周鲲领着魏鹏来到大厅,对着大家大声的介绍着:『大家静一静,这位就是
我的搭档也是咱们鲲鹏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大律师魏鹏先生,老的员工都认识,新
来的没见过,大家都认识一下,我们这个事务所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和他的』人群
里『嗡』的一声交头接耳了起来,有人悄悄的问旁边的同事询问这个老板的过往,
以前进事务所的时候也知道有这么个老板,可一直也没见过,也不知道干嘛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已经习惯了周老板而忘记了魏老板,突然魏老板冒了出来,
大家还有些不适应。
认识的人已经开始打招呼:『鹏哥,鹏哥』的叫着,不认识的有喊『老板』
的,有喊『魏大律师』的不一而足。
魏鹏双手摆了摆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沉声的说道:『谢谢大家的热情,我离开
咱们事务所已经有三个年头了,因为个人原因暂时去了国外,事务所的一切都是
我的好兄弟好搭档阿鲲一个人在苦苦支撑,我很感激,老的员工不知道我去哪里
了,新的员工更是不认识我这个人,没事的,我回来了,我还是我,我还是以前
那个魏鹏,我会像以前一样兢兢业业的工作,勤勤恳恳的带着每一位兄弟姐妹发
财……』当说道发财的时候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魏鹏摆了摆手笑着继
续说:『说发财的时候有的人在笑,心里会说这个老板真粗俗,我们这样为人民
声张正义的职业被说的充满了臭铜气,可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粮不聚兵
嘛,大家也是要吃饭睡觉,要娶老婆嫁良婿过日子,所以虚的我就不说了,必先
利其器我就是要大家赚到钱,赚到大钱,才能在我这里安心的善其事,下午和阿
鲲商量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还是主要负责法律事务这一块,我则负责事务所外
围的事情』魏鹏说完后看了看旁边的周鲲点了点头,周鲲开口说道:『刚才鹏哥
说了以后我们俩的分工,我很惋惜,很惋惜因为魏大律师的分工让我们的广大人
民少了一个强力的法律援助者……』周鲲的话还没有说完魏鹏就捶了他一拳大声
说道:『好了,大家别听他咧咧了,大家把手头的工作安排一下,今晚去屏东路
大富豪不醉不归,完了咱们再去好迪乐唱歌』听到了魏鹏的话大家一阵欢呼,各
自回头准备去了。
往酒店的途中给庄慧挂了个电话,说今晚和员工一起喝酒唱歌,大约回家晚
些,让她自己吃饭先睡不要等自己了。电话里庄慧温柔的嘱咐魏鹏少喝酒,早些
回来,她挺想他。庄慧还告诉魏鹏今天自己浑身酸痛没上班,魏鹏听到后哈哈一
笑说:『老婆,晚上洗白白等我哈……』庄慧在电话那头啐了一口说了道:『今
晚不伺候,老娘累死了,你这头驴……』两人又调笑了一番挂了电话,嘴上虽然
那么说,可是今晚使不能再折腾了,不光老婆累,自己也累啊。
刚挂了老婆电话周鲲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接通后周鲲在电话里骂骂咧咧的说
市里来了几个人大副主任,说是视察区里人民的公厕建设问题,区里要他们几个
代表作陪吃饭,满怀歉意的让魏鹏自己陪员工们吃饭,自己就不参加了,魏鹏告
诉他无所谓忙他的就是没事的。
晚上大家轮番给魏鹏敬酒,也不知道多少杯酒下肚,魏鹏脑袋嗡嗡响,实在
难受,姜小玉看到后就劝阻了陆续的敬酒者,魏鹏坐在一边抽烟休息,姜小玉端
来一杯白开水让他喝点醒醒酒,魏鹏问起怎么没见罗鑫,姜小玉说罗鑫去年就辞
职不干了,听听说去了南方省,具体在哪自己也不知道。
酒宴结束时已经九点多了,有家口的都回家了,还有一百多人留下要去唱歌,
当然这个唱歌也是有目的的唱,留下的大都是一些单身或者老婆在外地的。
到了沙滨大道好迪乐KTV时,只见卢永祥早早就在门口了,身后两排迎宾
小姐穿着快露出屁股的短裙,站在那里笑靥盈盈的等着。看到魏鹏的车停下后,
卢永祥快步早上前来,与走出车外的魏鹏紧紧的握着手说:『欢迎鹏哥的到来,
我都安排好了,你来之前打电话吩咐的事情我都办的脱脱的了,里边请』来之前
魏鹏告诉卢永祥自己这边一百多个色狼,一定要一人一个小姐,如果好迪乐这里
人不够就是去别的地方抢也要抢够了,打电话的时候都快九点了,让卢永祥去哪
里找这么多小姐啊,难为的要死,但是既然魏鹏开口了,他也不好推脱紧急的从
市里各个关系好的KTV、夜总会、洗浴中心、按摩馆等地借来了一批小姐,甭
管漂亮不漂亮只要是母的就行,这才凑齐了人。
在魏鹏等人进门的时候只见路上一辆辆的出租车吱嘎吱嘎接二连三的停在了
好迪乐的停车场,打开车门一个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快要露出屁股和胸脯的
姑娘们袅袅的往KTV走来。
卢永祥吩咐领班把一群眼冒淫光的色狼们领进一个个包间,还没安排完就已
经听到从有的包间没关闭的门里传出女子们淫荡的尖叫声,卢永祥单独把魏鹏领
进一个大包,刚要吩咐上酒水果盘,魏鹏身子一个趔趄扶住门边摆了摆手说:
『算了,我不玩了,今晚喝的难受,现在还想吐,本打算和你聊聊,算了……算
了……改天吧,今晚的费用你明天让人去事务所支款,我的回去了,难受』听到
魏鹏如此说,卢永祥也不矫情,因为他看到魏鹏的脸蜡黄,的确不时正常的颜色,
看来是真的喝多了。魏鹏把自己的车钥匙扔给卢永祥让他明天安排人给送到事务
所,自己打车回家,眼睛直晃开不了车了。
出租车刚到小区门口,魏鹏喊住了伺机要下车,在车上晃得厉害,想吐酒,
匆忙的付了账下车后走到小区门口背阴的花坛旁蹲下来嘴巴一张『呕……呕……』
的吐了起来。
一阵夜风刮过,吐酒后的魏鹏清醒了不少,自嘲般的摇了摇头呐呐的说自己
再也不喝了,真他妈难受。
点上一颗烟慢慢的踱步回家,快要到家时看到有个熟悉的人影在自己家门口
来回的踱着步子,手里还举着电话,定睛一看原来是庄慧,也不知道给谁打电话,
声音很轻也听不到她说什么,魏鹏想恶作剧的吓唬一下妻子,就悄悄的猫着腰往
前走,想给她一个背后拥抱。
快走近的时候却听到妻子在咯咯的笑,声音有些孟浪,嘴里还坏蛋坏蛋的喊
着,声音很低魏鹏听得不是很清楚,庄慧通话的时候身子还一扭一扭的,魏鹏很
奇怪这么晚了还跟谁通话,刚要悄悄的上前再听听时,庄慧却转过了身子往回走,
一眼看到猫着腰的魏鹏是呆愣了一下,拿着电话的手有些慌张的不知所措,不过
就一瞬间的呆滞,然后大声的对电话说:『刘婕啊,不跟你说了,我老公回来了,
明天去学校再聊,拜拜,然后也不管电话那头的声音就挂了电话。
『你干嘛啊,大半夜的,想吓死人啊,这么大个人了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
说完拍了拍胸脯长出一口气,好似被吓到了一样,路灯被树叶挡着看不清庄慧的
脸,魏鹏直起腰嘿嘿一笑说:『喝多了,早回家,看到你在打电话本想偷偷抱住
你,吓吓你呢,被你发现了』庄慧快步的走到魏鹏跟前搀着他的胳膊心疼得说:
『你就不能少喝点,喝多了伤身,快回家我给你做碗醒酒汤喝』两人一边走着魏
鹏一边随意的问道:『这么晚了,跟谁打电话呢,还跑出来打』『我刚做瑜伽回
来,还没进家门呢,我们系里的一个同事刘婕,我们俩是闺蜜,没事就通个电话,
一起做瑜伽来着,问问我回来了没有』庄慧用手轻轻的拂了一下散乱的头发轻声
的回答着,夜色昏暗灯光朦胧,魏鹏『嗯』了一声算是答应,可是庄慧的脸却有
些发烫竟然有些红了。
第06章
魏鹏回来已经一个月多了,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他很忙,先注册了
一个公司,自己又是法人代表又是公司员工,就是一个皮包公司,然后忙着跑新
区,暗中看好了几个地方,很有潜力,如果按照自己的计划一定能赚大钱,他把
所有关于这几个地方的资料都准备好以后,与周鲲碰了个面,想说一下粗略的意
向,周鲲说生意的事以后不用找他商量,让魏鹏自己拿主意,只是把魏鹏的每天
去向告诉他就行,方便他有事和魏鹏联系。魏鹏也无所谓,然后又让财务准备一
下启动资金,当然还要贷一批款子。
跟冯建国通过几次电话,还把庄慧父亲的*****告诉了他,让冯建国告诉
了他岳父,本想去拜访一下这位第一副市长,可是因为冯建国要去欧洲考察而推
迟了下去,关于商业用地的事魏鹏隐晦的提起过,冯建国含糊的点拨了一番表示
可以考虑,让魏鹏先把前期工作做好,银行贷款嘛可以去商业银行他可以和那边
打个招呼。
本来去银行跑贷款是财务部主管的范畴,可是凑巧家里出了点事,要请几天
假,银行的贷款魏鹏又不放心下面的人员去搞,只好自己去跑。提前和信贷部的
主任约好了时间一大早魏鹏来到商业银行的办公大楼,却被告知信贷主任有急事
去宜丰路分行了,如果有事就去那里找他,魏鹏只好驱车去这个储蓄分部。
停好车魏鹏走进大厅,大堂经理告诉他银行信贷科在十一楼,魏鹏走进电梯
按下楼层的按键,到八楼的时候电梯停了一下,一个丰满的女人低着头用脖颈夹
着电话出现在了电梯门口,两只手还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嘴里嗯嗯的答应着。
魏鹏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愣住了,这么巧!!进来的是王瑶,上身穿着小翻
领的深蓝女士OL西服,里面白衬衣的花边翻出西服之外,丰满的乳房很醒目的
鼓胀着夺人眼球,脖子上还系着一条空姐式的丝巾,下身是露膝盖的筒裙,白白
的大腿穿着肉色丝袜看得人有些晃眼,脚上穿着黑色职业高跟鞋性感十足。
女人刚要迈步进电梯,因为只顾着打电话,所以无意识的抬头下瞄了一眼电
梯里的男人,然后低下头继续打电话,可刚一低头女人又猛地抬起了头,满眼不
可思议的看着站在电梯里朝她微笑的男人,一时竟然忘记了说话,电话那头因为
女人突然的收声还在『喂……喂……』的喊着。
魏鹏看到直愣愣瞅着自己的女人,温柔的笑了笑然后指了指她的电话,女人
顿时回过神来对着电话急促的说道:『李主任,对……对不起……对不起啊,我
这里突然来了个重要客户,上午可能去不了你那里了,关于这次鸿宇经贸公司的
保函业务必须要等到他们资产剥离以后才能实行,我会好好的再准备一下材料,
等准备好了以后我再像您汇报……好的……好的……就这样啊……再见』王瑶挂
上电话慢慢的抬起臻首,默默的注视着眼前带着微笑的男人,这个让她朝思暮想
的男人。看着看着王瑶慢慢的依靠在电梯门边上,眼睛里泛起了泪花,晶莹的泪
珠从发红的眼眶里流了下来。
『妹子,还好吗?你……你……哭什么呀……好了……好了……别哭了……』
魏鹏最看不得女人哭,只要女人一哭他的心就软的一塌糊涂,快步走上前去,抹
了抹女人的眼泪,嘴里轻声的安稳道。
女人慢慢的把身体靠在魏鹏的怀里,把耳朵贴着他的胸膛,幽幽的说:『鹏
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来找我?我……我……我好想你……』魏鹏轻轻
的把王瑶揽紧怀里拍着她的背说:『回来一段时间了,我这……这……不是不想
再打扰你们的生活嘛……哎……哎……别打……别打了……让人看见就不好了』
王瑶听到魏鹏的话心里一阵酸楚,抬起头来梨花带雨的眼睛里满是幽怨,用自己
的小粉拳不断的捶着魏鹏的胸膛,嘴里还愤愤的不讲理的小声嚷着:『我就让人
看到……就让人看到……你个没良心的……』『好了……好了……别捶了,再捶
就犯心脏病了,你办公室在哪?我们去办公室谈,别在电梯里这样,搞得跟要殉
情似的,哎哎……哎……还打……』魏鹏安抚着怀里哭泣的女人,女人又是一顿
乱捶然后『噗哧』的笑了一声娇声的说道:『你才殉情呢,我还没活够呢,好日
子多着呢』说完从口袋里拿出纸巾擦了擦眼睛,然后掏出一串钥匙妩媚的看着他
说道:『我办公室在8018,这是钥匙,你自己开门进去,我去洗手间洗洗脸,
都怨你,害的人家伤心死了』魏鹏接过钥匙用手指套着钥匙环在手里转了个圈笑
着说:『去吧去吧,哭得跟小花猫似的,我自己去你办公室』王瑶踮起脚快速的
用嘴唇吻了一下魏鹏的嘴,转身袅袅的往洗手间走去。魏鹏在后面看着王瑶走路
时扭动的翘臀,那一肩的大波浪秀发,还有那白花花的大腿不由得咽了口唾沫在
心里说了一句『真他妈够劲』一股邪火顿时从心里冒了出来。
打开王瑶的办公室自己捏了点茶叶倒上水坐到沙发上,然后点上一颗烟随意
的打量着这件办公室。
办公室不大也就三十个平方,地上铺着棕色的地毯很干净,一张大大的办公
桌放在大玻璃窗前,桌子只有一台电脑,其它的就是办公用具,文件很多散乱的
放着。桌前是两颗不高的绿色植物,空调还在开放状态,凉风一阵阵的吹着,桌
子旁边是两个书柜,里面都是一些银行方面的书籍,还有一部分文件夹,书籍不
是很新,有些书籍的边角已经看到了磨损的痕迹,看来这不是装门面的,王瑶这
个女人真的在看这些书,而且从磨损方面来看,看过还不止一次。
职业的习惯让魏鹏看到每一件事物的时候都喜欢在心里分析。桌子左下角有
一双棕色的平跟女皮鞋,从他这个角度只看到露在外面的两只后鞋跟,大概王瑶
在办公室的时间很长,回来后就换上,这样也舒服些。
右面墙上挂着一副字『宁静致远』,再无其他装饰。
一只烟灰缸放在茶几上,上面很整洁,茶几上面和下面没有烟盒,屋子里也
没有烟味,大概王瑶抽烟的习惯已经改了吧。门口挂衣架上挂着几件职业女装颜
色大同小异,只是样式不同罢了,没有鲜艳的颜色,看来这个女人已经把自己摆
到了正统的道路上。
魏鹏思绪正在散乱的分析着,办公室的门轻轻的打开了,进门的时候还通着
电话:『……好的,小蒋啊我现在办公室里来了个重要客户,有事就打电话,如
果有客户帮我接待一下,我要谈重要事情……嗯……好的……那件事就这样办…
…好的……再见……』王瑶挂上电话笑意盈盈的走进来,随手把门带上还把保险
也插上了。
『鹏哥你自己倒水了呀,我还怕你自己不知道倒水呢,嘻嘻……』看到王瑶
进来了,魏鹏微笑的站了起来走到女人身边把她搂在了怀里。
王瑶因为魏鹏的拥抱身子微微的僵了一下,然后抬起头两人的嘴唇黏在了一
起,女人闭着眼睛环抱着男人的腰,激动得回应着男人的热吻,两条舌头互相的
缠绕吮吸,女人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硕大的乳房挤压着男人的胸膛,随着接
吻的幅度而来回的按摩着男人的胸膛。
一只魔手伸进了女人的衣服里,把乳罩粗野的翻上去,使劲的抓住了涌出来
的奶子,当手在揉捏她乳房的时候,女人脸上露出了很享受的表情,一只手放到
了后面抓着男人的臀搓捏着,另一只手则伸进了男人的裤子里握住了已经怒涨的
阳具,那滚烫和坚硬让她一阵心悸,男性生殖器的凹凸感从手心传来熟悉又陌生,
两腿之间忍不住已经潺潺溪流了。
迫不及待掀起女人的裙子手直接伸进了女人的三角内裤里,按在了湿滑泥泞
的阴户上,女人浑身痉挛着,两条腿使劲的并了起来,夹住了在阴户上搓弄的大
手。艰难的离开男人的嘴唇,趴在魏鹏的肩膀上,抓住阳具的手还不停的套弄,
嘴里有气无力的说:『鹏哥,操我吧,想死我了……』听到王瑶的哀求,在这样
的环境中又是和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女性互相暧昧的抚摸着对方的生殖器,这种刺
激真是前所未有,而胯下被小手套弄的阳具更是有些急不可耐的想进一步去探索
女性的身体,让魏鹏兽性大发。
把女人抱起来放到办公桌上,女人轻轻的褪下粉色内裤劈开大腿半躺在桌子
上,幽黑的阴户对着魏鹏,被淫水浸湿的阴毛一簇簇紧贴着大腿内侧,两片阴唇
因为充血呈现出蝴蝶的状态,随着阴道的收缩而一扇一扇的。两条玉腿大张,淫
荡的画面冲击着魏鹏的视觉,王瑶一只手撑着身体一只手逗弄着自己的阴蒂,眯
着眼睛发骚的求着男人:『老公……来呀……嗯嗯……嗯……来操我呀,你看…
…留了好多水哦……来啊……进来呀……人家受不了了啦……』魏鹏跪在桌子前
把整个脸埋进了女人的两腿之间,伸出舌头转圈舔着不断张合的阴道口,稀溜溜
吸着流下来的淫水,用牙齿轻轻的咬弄着两片肥唇,女人『啊……』的一声大叫,
使劲的抓住魏鹏的头发,把他的脸狠狠的按在了阴户上,屁股不断的往前挺着使
劲磨着,就像是要把男人的头直接按进阴道里一样。
『老公……别……别折磨老婆了……快进来……快啊……我要啊……操我啊
……老公……鹏……哥……求你了……快快……小屄受不了了……亲哥哥呀……
快插我啊……要死人了……』王瑶不停的扭动着身体,嘴里期期艾艾的哀求着魏
鹏快干她,他记得魏鹏喜欢自己喊他老公,于是不停的哀求着,因为这种隔靴搔
痒的感觉让她越发的难受起来。
魏鹏依然故我的舔弄着王瑶淫水泛滥的阴户,对王瑶的哀求置之不理。受不
了的女人猛地跳下桌子把坏笑着的魏鹏按倒在地,快速的解开男人的腰带把裤子
和内裤褪到膝盖的位置就不管了,迫不及待的跨到魏鹏的身上,抓住象旗杆一样
挺立的粗大阳具在自己的阴户上来回的蹭着,嘴里还『啊啊……』的叫着,然后
扶着阳具对准自己的阴道狠狠的坐了下去
第07章
两人同时的『哦』了一声,魏鹏闭上了眼睛,很享受阳具被一片泥泞包裹,
王瑶的阴道还似以前一样宽大,不过装下魏鹏这样巨大生殖器还显得有些空间不
足,『噗哧』一声,巨大的阳具把阴道里的淫水挤了出来,打湿了男人的阴毛顺
着阴囊淌到了地毯上。
当阳具滑入阴道,王瑶爽的胡乱着摆着头,闭着眼睛把衬衣扣子撕开,硕大
的奶子喷涌而出,两只手抓着自己的乳房上下挺动着自己的身体大声叫着:『啊
……爽……真爽……要死了……要死了……满……好满……亲哥哥呀……爽死妹
妹了……抓我的奶子……抓我呀……操死……我……哦……』看到身上女人疯狂
摆动身体兴奋的样子,魏鹏不断的往上挺着屁股,使阳具在每一次女人落下时都
能插到极限,双手抓住王瑶的两个乳房粗野的搓揉起来,王瑶两只手撑在魏鹏的
胸膛上,屁股高高抬起狠狠落下,吧唧吧唧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回荡,穿着高跟鞋
的脚使劲的撑在地上,蛮力的蹬着地毯,张力十足。
女人在在自己身上狂野的驰骋,刺激着魏鹏的神经,他一只手继续搓揉着女
人的奶子一只手啪啪的打着女人的屁股,虐待的快感让王瑶大大的张着嘴巴口水
往外留着,更加癫狂的耸动起来。丝袜也在这种疯狂中变得破烂不堪。
王瑶疯狂的耸动着身体,就像要把这三年没做的爱都找回来一般。突然女人
眼睛大大的张开,嘴里急促的呼吸着,大声叫着:『来了要来了……啊……啊啊
……丢了……丢了……高潮了……老公使劲……亲哥哥吖……来了……啊啊啊…
…啊……』只觉得女人阴道一阵阵极速急促的收缩,随着女人扭动的屁股一股热
浪彭涌而出,舒服的魏鹏直哼哼,女人大叫了一声身子软软的趴在他身上两只手
无力的垂了下去。
『哼哼……就这么完了……你老公还没爽呢……』嘴里恶狠狠的说完一翻身
把女人压到地毯上,用脚把裤子蹬下去扯掉自己的内裤,抓着依旧坚硬的阳具趴
在了女人两腿之间,用龟头研磨着淌水的阴户。
王瑶瞪着眼睛脸上带着高潮特有的红晕,嘴里呻吟着两腿大大的张开,两只
脚高高的翘起,脚上的高跟鞋一颠一颠的,双手扒着自己的阴唇哀求道:『来…
…快进来……我要……要嘛……老公……让老婆……让妹妹……上天吧……操我
……操……我……操我的小屄……啊……』听着王瑶的淫荡哀求,看着面前这么
淫骚的姿势,魏鹏恶狠狠的说道:『妈的,刚才是被你强奸了,现在让你这个小
浪屄尝尝被强奸的滋味……』用手套弄了两下龟头对准还在咕咕冒着淫水的阴道
使劲插了进去,王瑶只感觉一只巨物瞬间填满了自己的阴道,那种被插入的快感
让她浑身微微痉挛了起来,两只手抓着自己的奶头使劲的揪着,嘴巴大张,随着
阳具的抽插,嘴巴大大的张开却发不出一丝声音。
魏鹏快速的抽插着淫水纷飞的阴道,一只手掐着女人的脖子嘴里狠狠的喊着:
『操死你……操死你这个骚屄……妈的……操死你……』王瑶在男人虐待般的抽
插下高潮连连,窒息的快感让身子僵直的使劲挺着,两只脚胡乱的在地毯上乱蹬,
一直高跟鞋已经掉到了一边,雪白的玉足直直的往前伸着,脚趾大大的撑开,两
手抓挠着魏鹏的后背,一道道血痕触目惊心。
一阵要射精的快意迅速的来临,魏鹏松开双手撑在地上,狠狠的冲刺了几下,
股股滚热的精液射进了王瑶的阴道里,屁股往前又在女人阴道里耸了耸缓缓抽出
阳具,精液慢慢流出女人的阴道,王瑶则快速起身用嘴含住男人的生殖器滋溜滋
溜的吮吸起来,把阳具上的残留精液用舌头清理了干净,然后做了个吞咽的动作,
还伸出小舌头给魏鹏看了看,往地上一躺拉着魏鹏趴在了她的身上。
办公室里静悄悄的更凸显了男女粗重喘息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淫靡气息,
不知过了多久女人的腿慢慢的伸直,长长的喘了口气慢慢说道:『嗯……真爽啊
……都忘记被男人要是什么滋味了,嘻嘻……鹏哥……我好想你……我……我好
爱你……真的,也许我没有资格这样说,但这是我的权力,谁也阻止不了……』
说话的时候女人眼睛红了,两行泪水顺着眼角慢慢淌了下来。
魏鹏没有说话翻身平躺下来深深的呼了口气,伸手拿起茶几上的烟盒,女人
擦了一把眼泪坐起来抓过男人手里的烟盒取出一只放进他的嘴里伸手拿起火机帮
他点上,然后乖巧的卷缩在魏鹏怀里,眼泪还是止不住的流着。
『妹子,我知道你的心意,可我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我给不了你想要的,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看到你今天拥有的一切我很高兴,真的,打心里面高兴可…
…』『……别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说过让我抛弃以前的生活,重新
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听你的,我不怕,我不会的我可以学,学不会也没事,
我有时间,我一天睡四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拼命的学,我心里有你,我改,我
改掉以前的所有不好,我要做你的女人,鹏哥我知道你不喜欢麻烦,我知道你不
喜欢给你带来麻烦的女人,我不拖累你,我现在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我没
有……没有靠自己的身体去……去取悦别的男人……呜呜……我只要你喜欢我…
…』王瑶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伤心的用手捶打着魏鹏的胸膛。
看到女人伤心的哭泣,听着女人哀怨的话语,魏鹏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化了,
他见不得女人哭,尤其是和他发生了性关系的女人,灭掉手里的香烟,双手楼主
女人轻轻摸索着女人的脊梁『……』呐呐的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女人慢慢止住了哭声用手胡乱擦了擦眼泪看着魏鹏问道『……鹏哥……我喜
欢你这样霸道的男人,你有一个家,你呵护你的妻子,就算她那般的不是,你也
依旧不放弃,你为她做的这一切让我发疯般的嫉妒,为什么我王瑶就没这么好命,
没有这样一个男人包容我爱护我……但我认命了……我不去挣她的地位,能遇到
你是我的福气,你说过让我做你的女人,不让别的男人碰我的身子,我都听你的,
我以前是个婊子,但是自从你说过以后,我就把自己当作你的女人了,我拼命的
改变我自己也是因为你,我只要你的心里给我一个地方,好吗?……』魏鹏心肠
很硬,那是在法庭上,作为一个律师心肠不狠是不行的,他需要理性的控制自己
的感情,因为在法律面前,个人的感情毫无作用。
但是对眼前这个女人他犹豫了,虽然和她有过几次肌肤之亲,也曾经些心动,
那也是因为他喜欢女人直接大胆的表达方式和聪慧,却没有心动到把她接纳进自
己生活中的地步,家里又出了庄慧和儿子乱伦这样的事情,让他觉得女人多了好
麻烦,能不招惹还是别去招惹的,可此时王瑶的大胆表白让他心里起了阵阵涟漪,
他心软了,一个这样死心塌地爱着他的女人,他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抿心自问
自己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在非洲的这几年脑子里想的最多的是庄慧,可是邓雪、王瑶、余佑君……自
己难道忘记过吗?他是风月场的老手,接触过有过性交行为的女子数不胜数,为
什么就对这几个女子念念不忘呢?那是因为这些各有特色的女子已经悄悄的在他
心里有了一席之地,只是他不承认罢了,男人哪个不喜欢三妻四妾,王瑶爱他,
他也喜欢王瑶,还装什么大尾巴狼?!!
『瑶瑶,给我适应的时间,我喜欢你,我承认,我没有忘记你,我本来不想
再和你见面,只是想让你这样安静的去过自己的生活找个好的男人嫁了,忘记过
去的一切,幸福的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但是你是我魏鹏的女人,那么我就不许
你再找别的男人,只属于我,我会照顾你的一切,我现在有个大计划,等我赚够
了钱,就会让你们过上不一样的生活……』王瑶听到魏鹏叫她『瑶瑶』心里一阵
激动,后面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她知道魏鹏已经把她装在了心里,泪水又止不
住的流了下来,咧着嘴又笑又哭的不知道说什么,唯一的表达方式就是疯狂的去
吻魏鹏。
『哎哎……好了好了……别再亲了,再把我的火惹起来……』『谁怕谁,我
就要你……要你……你是我的男人了……我要你……』『哦……嘶……轻点……
咬断了……硬了……又硬了……哦哦……瑶瑶……』『老公……好大呀……好硬
啊……老公要我……老公干我……干……我……老公使劲操我……啊啊……嗯嗯
……啊老公……进来了……哦好满哦……老公操我……啊……』只见女人的双腿
在空中颤啊颤的颠了起来两具身体又疯狂的缠绕在了一起。时间慢慢流逝随着两
人长长的一声『哦……』男人慢慢的趴在了女人身上,遂即传来两人咯咯的笑声,
很愉悦很畅快。
魏鹏起身拍了拍女人的屁股示意该打扫战场了,王瑶让他坐到到沙发上,说
这是女人该干的事情,还俏皮的说了声请大老爷安坐歇息,妾身收拾就是。
王瑶先用毛巾仔细的把魏鹏下身擦拭干净,温柔的帮他穿上裤子倒上水放到
男人的手里,然后收拾地上的杂物,脱下自己所有衣物光着身子擦拭完自己的下
身,走到办公桌前从最下面带锁的抽屉里拿出内衣裤穿好,把旧的衣服放到一个
衣物袋里,换下了已经破损的丝袜,拿起挂衣架上的衣服穿好,穿上那双平底皮
鞋,梳了梳自己的乱发用皮筋熟练的挽了几下束好,一个光鲜的办公室女郎出现
在魏鹏面前。
『呵呵,看你梳妆也是一种享受啊,瑶瑶你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气质的变化
大了去了,看来时间真的会改变很多事啊』魏鹏手捧着茶杯,眼睛明亮的看着站
在面前靓丽的女人,乐呵呵夸奖着。
王瑶婷婷的走到沙发旁轻轻的坐下挽住魏鹏的胳膊,歪头靠着他的肩膀闭上
眼睛,脸上出现了很享受的表情轻声的说道:『老公,我心里好高兴,我也有男
人了,嘻嘻,靠在你的肩膀上真踏实』『瑶瑶,我看你办公室里怎么还放着内衣
啊?』魏鹏拍了拍王瑶的小手轻声的问道。
『我在办公室的时间比家里还长,有时候连着几天工作晚了就在沙发上凑合,
女人嘛不能几天穿着一套内衣吧,只好在办公室里换啦。小毅在外地上大学一年
回不来几次,我一个人在家孤零零的,所以我把只好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了,看到没这些……这些……都是我看过的书,这是我前半辈子想都不敢想的事
……嘻嘻……』
第08章
王瑶松开魏鹏的胳膊站起来走到书柜旁,打开橱门邀功一般的对他说:『这
是《商业银行会计实务》这是《银行经营管理实训》《货币银行学》《信贷行业
法规及综合能力》《投资与控股》这些……这些……这些……我都看完了,刚看
的时候跟看天书一样,我从最开始的会计入门学起,到现在都不记得看过多少书
了,通过你们事务所的关系来到这个银行的时候,是先从柜员做起的,开始我什
么也不懂,总是出错,好歹看你们事务所是储蓄大户存款的面子上没有解雇我,
我当时就很不服气,他们都行凭什么我不行,于是我就拼命的学习白天上班,晚
上报补习班,不会的就问就查资料,笨鸟先飞嘛……嘻嘻……』『他们不敢解雇
你,我们事务所是你们这个储蓄分部的VIP,你可以去找周鲲啊,让他给你撑
腰,你又不是不认识他……好了瑶瑶,别站着了过来说』魏鹏静静的听着王瑶的
叙述,拍了拍沙发,他知道现在王瑶需要一个倾听者,在爱的人面前说说她的苦
痛和喜悦。
『我没去找周鹏,我是你的女人,我还是少去找别的男人为好,我只有你这
一个男人,我不需要求他们……呀……都十一点多了,咱们吃饭去吧,折腾这么
久你不累呀我可累了,走啦……咱们吃西餐去,我请客』王瑶看了看表拉起魏鹏
撒娇的说道。
『哎呦……嘶……你慢点拉我,我的背上被你抓得现在好疼,你刚才像要吃
了我一样,再这样几次我就报销了……哈哈……别打啦……哈哈……』魏鹏站起
时背上一阵刺痛,咧着嘴打趣的逗着王瑶。
王瑶心疼的用小手捋了捋听到魏鹏的话用手拍了一下男人结实的脊背,轻轻
的啐乐一口递给了魏鹏一个卫生眼,快速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按了几个数字:
『小蒋啊,你安排一个午餐……嗯……西餐……两个人……对……不去那家……
嗯……去金牛角西餐厅吧……也是我们的大储户……一次也没去过不好……好的
……三十分钟后到……再见……』魏鹏静静的看着这个以前靠出卖肉体而生活的
女子感叹不已,面前这个女人已经不需要用身体去取悦男人了当然自己除外,她
变了,变得干练、独立、有思想、有心机了,通过刚才的电话可以看出:一、她
现在已经有了作为人上人的那种气度。
二、她说话的时候没有废话,条理很清楚,这是作为管理着必备的要素。
三、对事情的把握度很到位,去这家餐厅是因为从没去过,那里的招待不认
识她,这样就给了他和她更好的宽松空间。
四、去吃饭还顺便照顾大储户,一举两得,以后面对储户的时候也好说话。
不简单啊,变化好大,以前遇事只会哭鼻子的小女人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
出于职业的习惯魏鹏在心里分析着。
『走啦……发什么愣啊……』王瑶挂上电话,伸手挽住魏鹏的胳膊,拉着他
走出来办公室。
走进餐厅在侍者的引导下俩人坐到了已经订好的位子上,王瑶向侍者熟练的
点了餐还要了一瓶价格不菲的红酒。
『瑶瑶,以后别这么累了,该休息休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做事慢慢来,
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呵呵……』魏鹏给王瑶倒上红酒轻轻的对王瑶说。
『我已经习惯了现在的节奏,这样挺好,走到哪里都会得到别人的尊重,我
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所有的自信也都是你给我的,我坚信有一天你会让我
走进你的心里,我是你的女人,你是我的男人,过去的王瑶已经没有了,现在我
才是我真正的我……』王瑶慢慢摇着杯里的红酒,含情脉脉倾诉着自己的爱意。
魏鹏从王瑶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执着,对心中爱情的执着,那是一种坚定的
信念,很炽热很纯洁的那种,就像热恋中的少女看到了心中一直崇拜的白马王子
一样狂热。魏鹏心里突然产生了种自惭形秽,现在的王瑶很美丽,从内到外释放
者一种脱俗的光芒,就像女神艾芙萝黛蒂,魏鹏紧紧的握住王瑶放在桌上的手,
用温柔的眼光看着眼前的女人心里发出阵阵的感动。
『放心吧,既然我承诺了就不会改变,我虽然不能给你一个名分,但是我会
尽力的为你做到一切,你是我魏鹏的女人,今生都是,我会告诉我的亲朋好友,
你是我的女人,不会改变……』魏鹏握着王瑶的手眼中闪现着认真的光芒对女人
郑重的说道。
王瑶好看的眼睛一阵湿润,眼泪在眼眶里转着,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
听到了自己心仪男人的承诺,什么名分什么地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男人把
自己装到了心里,从此自己也有了依靠和寄托。看到侍者端来点好的菜品,王瑶
掩饰得擦了擦快要流出的泪水,魏鹏松开王瑶的手轻声的问道:『小毅还好吧?』
『小毅很好,在大学里阳光开朗,我和他的那种关系已经不存在了,我努力的工
作,他努力的学习,呵呵,我们母子想的开,并没有让这件事情影响我们,他也
找了女朋友了,过年的时候领回来给我看过,很清秀的一个女孩……你们家那位
呢?现在好吧?』侍者离开以后,王瑶在魏鹏面前没有什么顾忌的说着她和儿子,
也没有去掩藏什么,说的很自然。
『嗯,挺好的,一切都回到了正轨上,小……宇和小雯出国了,我妈还有岳
父一家都在新西兰,现在就我和庄慧一人在家,我现在正在你们银行跑一批贷款,
大概要七千万吧?上午去你们总行,信贷主任去你们分部了,我就到了你们那里,
这不是……见到你了吗……』『怎么贷这么多?总行的信贷呀?那我可帮不了你,
你们事务所贷款干嘛?你个没良心的知道我在银行也不来找我……』王瑶听到魏
鹏的话有些小吃惊然后幽怨的看着他,嗔怪魏鹏的绝情。
『我在玉东新区看好了几块地皮,想通过关系拍下来,估计启动资金在一亿
左右,我自己这里也就几千万,所以资金缺口大了些,事务所法律那块周鲲抓总,
我现在主要是搞外围,面对王瑶的幽怨魏鹏没有回答而是轻轻的避了过去。
王瑶听出了魏鹏的意思,也没有去追问,只是就银行贷款的一些事情帮魏鹏
详细的分析了一番。
吃过午餐王瑶离上班还有一段时间,两人就来到了餐厅对面的咖啡屋小憩,
进了小包间王瑶点了一杯卡布基诺,魏鹏要了一杯红茶,他喝不惯那玩意跟中药
汤似的,两人坐在一起互相依偎着。
魏鹏说起回来这些天的动向,当提到回来后跟庄慧出去玩了一段时间时王瑶
有些嫉妒的说道:『我真嫉妒你们家庄慧,同样是女人,她的命真好,有你这么
个老公宠着,想想都让人羡慕,不管她做什么你都那么包容她……』『你也是我
的女人了,我以后也会宠着你的,我的女神艾芙萝黛蒂……』魏鹏轻轻的握住王
瑶的小手拍着她的手背一脸微笑的看着王瑶。
王瑶紧紧抓住魏鹏的手深情的凝望着对方的眼睛,眼里泛着泪花感动的说道:
『你个坏老公,说的人家高兴的想哭……』,魏鹏搂着怀里的女人轻声的安慰,
不时的还吻一下女人的头发。
『其事女人也很容易满足啦,只要有个疼她爱她心里有她的男人就知足了,
像我这样整天的忙碌,何尝不想有这样一个温暖的胸膛让我依靠呢』在魏鹏怀里
撒娇般的拱了拱,王瑶很满足的说道。
『庄慧也应该知足了,她有你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她上班清闲老公又是
个律师,还有能力赚钱,想想做梦都会笑哦,不过……女人太清闲了也不好,向
你们这样在一起久了难免的会激情殆尽,我也是女人……我……接触过她几次,
我也是女人,我知道女人被宠坏了可不是好事,她那么漂亮高贵就是太率性而为
了,你……你得好好看着她……』王瑶期期艾艾的说着话。
魏鹏听王瑶的话眉头微微的皱起,有些不悦的说:『好了我知道分寸,她已
经改了,不过就是和小……,算了不说啦,除了这件事她在其它方面还是挺自重
的……』魏鹏心里总觉得庄慧母子乱伦的事情只是家事,毕竟那是有原因的,也
不全怪庄慧,庄慧也没有在外面勾勾搭搭,曹曦曾说过庄慧有强烈的精神妄想依
赖症,也就是精神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都过去了,今天王瑶说起庄慧让他心
里一阵不悦,感觉王瑶有些越俎代庖了。
抬起头看到魏鹏脸上不悦的表情,王瑶知趣的闭上了嘴巴没有说什么,俩人
并没有因为这样谈话而尴尬,依旧卿卿我我的温存到王瑶快上班的时间才离去,
魏鹏把王瑶送到银行楼下,王瑶在下车的时候捧着魏鹏的脸深深的吻了一下,然
后把自己新家的地址记录给魏鹏,还留下了一把钥匙,然后打开车门站在车外打
手势让魏鹏先走自己在这里目送。
魏鹏按下玻璃努了努嘴做了个亲吻的表情,说了声拜拜缓缓的把车开走了。
『鹏哥,庄慧这个女人不简单,你是当局者迷啊,她就是个婊子,虽然我以
前也是,但我和她不是一样的,唉……』王瑶看着远去的汽车默默的在心里想着,
叹了口气转身往银行大门走去。
满脑子新区地皮和贷款的事情,魏鹏早把王瑶的话抛之脑后了,今天因为有
这段插曲,贷款的事只好明天了,事务所也不想去,还是回家吧。
在路上想给周鲲打个电话说些事情,但是对方无人接听,看看时间才下午一
点半,这小子忙什么呢电话也不接,当车子开到锦西大道路口等红灯的时候,远
远的看到周鲲搂着一个女人走出了一家高档宾馆的大门,抬手招呼了一辆出租车,
在车边与女人又抱了抱,把女人送上了车,朝着出租车挥了挥手,就站在那里看
着车子远去。
因为离得远又是在等红灯,如果不是熟悉周鲲的背影,魏鹏也认不出来,但
是他怀里的女人就看不清了,因为周鲲的搂抱,女人只露出三分之一的身体,是
看了飘动长发和在上车的瞬间才确定是个女人。
『这个淫棍,大白天的就泄火,真他妈腐败……也不怕别人瞅他脚后跟,被
人揭发包二奶的事他这么快就忘了……』魏鹏脸上带着笑心里微微的诽腹着。
过了绿灯车子开到宾馆的路边,魏鹏按下玻璃窗,大声喊住了正要开自己车
门的周鲲。周鲲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转过身来到处寻找,当看到路边车上对
着自己打手势的魏鹏时,脸色瞬间有些白,不过也就是刹那,也许是日头暴晒的
缘故,周鲲手打着凉棚慢慢朝魏鹏走过去。
【待续】


